今天我要提出两个一般性的主张, 并通过对19世纪西方现代火葬之出现的一项研究, 展开论述。第一个主张关于亡者。思考亡者是有益的, 因为他们是如此密切、如此典型地构成了生者之想象世界的一部分。①思考亡者——作为自然事实、对象、受化学支配的肉体、个人, 作为父母和祖先, 作为人的符号、人的遗留物、文化伦理主题等等——是建构和界定文明的一种行动。
第二个主张关于历史解释。我将指出, 历史解释并不在于显示, 那些我们想要解释的问题遵循着某种类似普遍原理的法则, 例如, 特殊性是普遍性的个案。我的理解是:在文化历史研究中, 历史解释是一种阐释意义的过程, 我们试图在各种发展、思想、运动和意义的关系之中展开这种意义阐释。我将对特定情境做出具体介绍, 以论证我的主张。
具体来考虑如下历史问题:从1870年代开始,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 现在应该适时地抛弃长达将近两千年之久的安葬死者(尸体)的传统, 改用技术成熟的焚化炉对死者作火化处理。20世纪初, 西欧和北美出现火葬记载。到了1950年代, 火葬已经成为寻常之事甚或占据主导地位。至此, 我的描述中包含了几个历史阶段, 我将着眼于早期阶段。
为什么西方世界(自古代以后)直到19世纪末才首次实行火葬?为什么当时会引发如此激烈的辩论?如果我们从一些既存的、一般性的原因来看, 这些问题会令人迷惑不解。这些原因是:当时并没有新的发现足以支持火葬比土葬更有益于公共健康; 更何况当时恰逢美观整洁的新式公墓全面取代陈旧拥挤的教堂墓地; 火葬, 哪怕具备一切令人信服的条件, 在经济上却不比土葬便宜; 无论对死亡或亡者, 人们的态度一如既往, 没有出现偏爱火葬的新态度, 也没有人突然转向印度教或佛教从而在宗教基础上信仰火葬。受东方宗教影响的有灵论者(spiritualist)赞成将死者的微粒迅即地送往宇宙, 但这并不是关于死亡的一种新态度。对于这些主题,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 在1870年以前都没有出现任何正式且重要的观点, 而只有一些随意和边缘的想法。
换言之, 很难去解释, 欧洲当时缘何提议改变对死者的安置方式——将土葬这一自基督教兴起以来安置死者的唯一方式改为火葬, 这既不能被解释为科学发现的结果、经济上的必要, 也无法归因于对死亡的新观念。然而, 各种引发争论的行业性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美学的、宗教的方案确实发生了竞争, 以获得文化权威。这些方案争取权威地位的途径是, 公开地阐明关于处理死者尸体问题的观点, 并将这些观点付诸实施:用焚化炉将死者的尸体快速地化为灰烬。
在这篇演讲中我想要表明, 对现代火葬之出现及其命运的解释, 不是要做一种更深的挖掘, 而是力求一种更宽阔的开拓, 扩展出一个阐释性的网状结构。而我关于火葬的主张将在各种关系之中予以构建, 这些关系包括:与新古典主义和古代的关系、与废物处理、与社会主义、与宗教精神、与神秘学、与非正统基督教、与卫生工程、与城市规划、与医学、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我们要在所有这些场域中来广泛地思考死亡对文化的作用, 也就是说, 是经由死亡, 当代人指出了一些普遍和困难的问题:关于历史、科学、理性和信仰在当下事件中的位置的问题, 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 关于尊敬与不敬的问题。
现在我将通过具体分析来阐明我的两个一般性主张。
建筑物中的焚化炉让我从建筑入手, 先来探讨焚化死者与其他关切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的可能基础相当多, 但并非无穷尽的。1939年,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的前城市规划主管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 是一位火葬建筑的专家。他认为, 容纳一个焚化尸体的熔炉, 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机械设备掩藏起来, 比如滑轮、液压升降机、轨道、出烟孔、曲颈蒸器等。无论在建筑上采取什么形式, 他认为都不如向哀悼者提供一种艺术(在美学上类似于止痛疗伤的香油)——在这个情况下, 形式不应该服从功能:“如果有人想到早期火葬场设计的形式需求, 他说, 那么就能将其理解为克服烟囱的一种美学努力。”①火葬场, 模仿教堂却又不同于教堂, 它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 火葬场像教堂一样提供一个空间, 在死亡与处理死者之间的有限时间内, 让未亡人在这个空间内向死者最后道别, 从音乐、仪式和美观的建筑中获得安慰; 在一些特殊的火葬场合, 还能凝望美丽的火焰, 它的洁净力量使灵魂快速地摆脱躯体的桎梏得以自由。而另一方面, 火葬场不同于教堂, 它的内核是与圣所完全不同的一种秩序。在地面上, 汉堡的火葬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工艺; 而在地下, 是非常沉重的机械设备。在地上, 古典的多特蒙德(Dortmund)火葬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圆形建筑; 而在地下, 管道、曲颈蒸器等等使现代无烟火葬成为可能。

|
图 1 多特蒙德火葬场和骨灰安置所其剖面图(图片来源:Schumacher, Die Feuerbetsattung, 59)。 |

|
图 2 多特蒙德火葬场和骨灰安置所其剖面图(图片来源:Schumacher, Die Feuerbetsattung, 59)。 |
现代技术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可以与旧式的美学相结合:火葬是清洁的, 同时又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与宗教情感及安慰仪式相兼容。两者所代表的两个范畴和两种视觉风格愉快地共存——一种是现代或历史风格的民间性或准宗教性建筑的建筑雕版或照片; 另一种是机械设备的蓝图或示意图, 这种结构的一些变体可能出现在钢铁厂或集中营。工程和宗教、焚化炉技术和礼拜, 可以联手一起为生者与死者服务。在意大利背景中, 教会谴责火葬割裂了传统仪式与葬礼的关联, 并迫使火葬倡导者走向意识形态的极端, 这两种形式的调和就变得更为迫切。意大利火葬协会联盟发布了如下声明:焚化技术必须被隔离在视线之外, 联盟将致力于提高其设备的仪式感和庄重性。该声明动议, 在下一个万圣节, 所有“火葬殿堂” (crematorium Temples)向公众开放, 人们可以向死者骨灰盒或他们想要“虔诚朝拜”的墓地献花。②
然而形式与内容的和解并非必然。巴黎和兰斯(Reims)的火葬设计者完全没有着力掩饰建筑内的焚化炉。马赛某火葬场的建筑师只是用东方建筑尖塔结构对显眼的烟囱稍作掩饰而已。但更重要的是, 当火葬被第一次提出时, 所有这些都还不是关键所在。
1885年, 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 火葬协会在其于沃金(Woking)购买的土地上建成一个巨大的伦敦郊区墓地, 这是火葬业的顶峰时期——不向艺术让步, 不向历史上任何已知的死亡美学妥协:它就是它所显现的那样, 即一个有着烟囱的焚化炉。这正是它想要的。其他火葬场试图以各种方式将生硬的现代技术与历史美学相调和。换言之, 火葬倡导者必须去思考, 他们想要在(代表进步、清洁和效率的)技术与(关怀死者的)悠久传统中构建怎样的关系。

|
图 3 巴黎的火葬场。巴黎的火葬场被一种更少工业感觉的设计所取代(图片来源:Schumacher, Die Feuerbetsattung, 797)。 |

|
图 4 兰斯的火葬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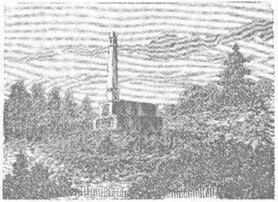
|
图 5 位于沃金的英国第一座火葬场(图片来源:Prosper de Pietra Santa, "La Cremation en France et Italie, "Journal d′hygiene 8(1882), 73)。 |
英国的火葬论者持有一个文化主张, 强调对尸体的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解释, 即死者的身体是——仅仅就是——一种尘土, 应该被当作尘土来对待和讨论。它们是不洁的, 如何处理它们是一个科学问题, 尤其是化学、医学、卫生和废物处理等(关注清洁的)学科的专家们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新观点和一群新的专业人士, 他们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主题上的见解将变得更重要, 随即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思考和实际处理尸体的方式。一位早期倡导者指出:“公共卫生(Sanitation) ”是现代火葬“真正的、主要的存在理由(raisond’être) ”, 作为其延伸, 公共卫生应该是如何处理死者的决定因素。亨利·汤普森(Henry Thompson)是当时最著名的泌尿外科医生、英国火葬协会创始人之一, 其著作被译成多个语种。他写道:“公共卫生法必须实施火葬或其他除土葬外的处理尸体的方法, 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做出死者身体“只是”死尸“而已”这一主张中, 关于死亡的那种巨大的文化历史力量被重申, 并被挪用作为对一种世界观的支持, 这种世界观可能恰恰会否定这一主张。①
汤普森留给后人一份关于火葬的谱系, 这是一种决然且有意识的浅薄叙事:起始于将尸体作为医生和公共卫生工程师的实验对象。我想要指出, 它本身就给出了一个文化论说:可以用一种完全技术的——经常是精神错乱的——方式来谈论死者。
汤普森说, 起初是意大利的医学教授在1860年代末期首先对焚烧人和动物的尸体予以实验。当汤普森看到4149号展品时, 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4149号展品是布鲁内提(Brunetti)教授的仪器及其产品, 即成堆的混杂骨灰和他的焚化炉模型, 展出于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布鲁内提的实验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但他的方法是原始的:实验用了3.5小时、150磅木头, 将一个成人(尸体)变成1.7公斤的精细白灰。②
1874年初, 他从维也纳返回后不久, 通过英国大机械厂的一种焚化炉, 得以将一个47磅的瘦弱之人的尸体变成1.75磅的骨灰, 仅用时25分钟。而一个粗壮乞丐重达140磅的尸体化为4磅的骨灰也只需要数十分钟。没有气味。“就视觉和嗅觉测试而言, 没有什么比它们(骨灰)更纯净; ”他写道, “一份废物”被转化为“一种优雅的扬弃(sublate) ”。还有一些补充研究。例如, 在1876年国际火葬问题大会上, 一篇论文报告了莱比锡的工程师斯蒂尔曼(Steermann)和雷克拉姆(Reclam)教授成功运用气体燃料——取代煤炭——来焚烧尸体, 死者是“一个被救济院放弃的抚恤金领取者”。①尸体焚烧的细节, 虽然是早期火葬倡导者的兴趣重点, 但无需我们在此予以关注, 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早期火葬倡导者对这些细节抱有何等强迫性的兴趣。参与竞争的设计充斥着相关文献。现在的要点就是:从冶金术借鉴得来的技术使尸体能够被彻底消耗(consume), 而不会污染空气, 也不会触碰到燃料。人的骨灰可以被提纯, 杂质经由曲颈蒸器下的腔膛被过滤干净。在这个新系统中, 尸体不再是带着献祭的联想而燃烧于旧式柴堆, 而是通过焚化炉的强热被消耗——被完全变形, 就像矿石被提炼成金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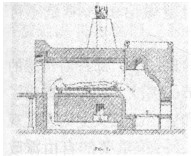
|
图 6 19世纪现代焚化炉的横截面图。这种焚化炉改良自钢制技术,使尸体在火化时不会碰到火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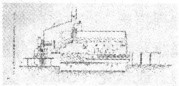
|
图 7 19世纪现代焚化炉的横截面图。这种焚化炉改良自钢制技术,使尸体在火化时不会碰到火焰。 |
污染——不是仪式上的而是生态学类别上的污染——对那些想要把死者视为废物的人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一本重要的公共卫生期刊《公共卫生记录》 (The Sanitary Record)上记载了1879年“不完全腐烂的死尸粒子散逸”的可能性所带来的“恐怖影响”, 但同时指出可以用烟囱内的焦炭防止这种可能性。②西门子(Siemens)焚化炉和其他技术发达、特别设计的焚化炉, 更少刺激感官, 更优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印度的火葬不同, 现代火葬是那种我们几乎可以称作“碳中性”的事物。
威廉·伊西斯(William Eassie)在1874年英国火葬协会成立之时被任命为协会秘书, 这标志着进一步将死亡当作自然事实——而非文化事实, 也就是让死亡归属卫生学家而非牧师的领域。伊西斯是一位著名作者, 他的著作成为当时建造健康房屋的标准手册, 提供如何选择合适的排水通风装置及“同类项目”的技术指南。不过, 伊西斯本人认为, 自己投入到了更宏大的世界历史规划之中, 而焚烧尸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终于, 公共卫生的时代来临了。”他写道。最后“人的自杀”将会“因藐视一切卫生法律而受到制止”。他指出:如果我们——我们英国人——“想要在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中保持自身的卓越”, 那么对公共健康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将获得胜利。”“事实——而非幻想——将必然成为我们的指引。”
从这里走到火葬及其历史只有一步之遥。伊西斯指出, 从最早的时代以来, 人们就基于公共卫生而焚烧尸体, 以“保护生者免于腐败物的侵扰”。如今我们知道其原因的细节。尸体在根本上被划归到排泄物类别。埃德蒙·帕克斯(Edmund Parkes)在其(被多次再版的)著作《实践卫生指南》 (Manual of Practical Hygiene)的一个章节中这样解释, “普通的伦敦下水道”的每加仑污水每小时会产生1—1.5立方英寸令人窒息的气体, 包括碳酸、硫化氢、氨的硫化物和“腐烂的有机蒸汽”的残渣, 其中“真菌和细菌滴虫”大量存在。对尸体有着类似的描述:关于下水道的章节之后是关于教会墓地空气的章节, 帕克斯指出, 伦敦的52000具尸体每年会产生250万立方英尺的碳酸, 同样是“真菌和滴虫大量存在”。③
但核心要点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 死者首先是一种废物——垃圾——因而必须被当作废物来处理:尸体与利兹城(Leeds)那些肮脏的室外厕所被粗略地相提并论。一位外科医生曾在对赫尔(Hull)文学协会所作的演讲中警告说, 英国每年大约会产生四百万腐烂的肉体; 准确地说, 如果以每具尸体含8英石重的腐烂物质, 那么仅赫尔一座城市, (每年)就会产生重达28791英石(约合403003磅)的腐烂肉体。④
对焚化炉建筑和公共卫生的讨论, 引发了未来主义的推测:一个在技术上或许不及西门子焚化炉发达的殡尸工厂, 却可能在仅仅5小时内——以煤气为燃料——焚烧大城市曼彻斯特一天内的所有尸体。一项关于霍乱的研究指出, 如果可以用气体作业的曲颈蒸器处理尸体, 那么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对环境的危害, 只是等同于一支工厂烟囱。”1875年, 当时的著名期刊《图解》 (The Graphic)提供了一份建立火葬殡仪礼堂的计划——有一点旧式文化的感觉——在数百码的城镇煤气厂内, 以液压方式经由地下通道, 将死者尸体从情感世界迁移到效益世界。①
死尸与政治生态学汤普森指出, 已经死去的人, 如同肥料和其他有机残余物, 是自然资本的一部分, 而“资本是要产生利息的”。埋葬尸体无异于埋葬收益, 而火化尸体才能使它们具备再度获利的可能。想一想, 他提示说, 伦敦每年有80430个死者, 可以产生206000至282000磅重的骨灰——比同样重量尚未火化的干尸价值高出6至8倍; 另外, 还能产生584000磅滋养植物的气体, 这是50至100年内无法自然产生的气体量。将这些数字乘以9 (如果以全国是伦敦的9倍来计算), 那么由整个国家的死者所产生的效益将是惊人的。②
以上这种修辞论述至少还可以追溯到生理学家雅各布·摩莱肖特(Jakob Moleschott)的著述。这位生于荷兰而在海德堡讲学的生理学家, 在三十年前就以如下观点著称, 即坚持认为, 磷盐(phosphoric salts)是大脑乃至文明发展必不可缺的物质——“没有磷, 就没有思想。”埋葬死者就是剥夺了人类竞赛中的这个关键元素, 因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原料离开了人体, 却留给了也许对其并无用处的贪婪的虫子。换言之, 尸体含有至关重要的可重复利用物质, 而将它们留在教会墓地, 使这些物质在一个世纪中都无所作为, 这简直是非理性, 好比相信人类献祭或巫术一样非理性。③
经由火葬通往现代性当然, 对于死者的安置, 从近两千年的土葬转向火葬, 这一形式转变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革新及其基于效益的偏好主张。这(即便并非不实)也不是故事的全部。
法国卫生学家桑塔(Prosper de Pietra Santa)批评他的米兰同事们将对火葬的拥护与政治观及宗教信仰混淆在一起。他认为:他们受制于对个人重要性的膨胀感觉, 仿佛以为“火葬在文明世界中的命运要仰仗于他们”。但是, 桑塔自己的工作却深深地浸透在政权还俗主义(laic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之中, 如此多地述及第三共和国的社会政策。这说明了他所期望做出的区隔是不可能的。④
在许多火葬论者的修辞论述中, 那种对情感的强烈拒斥, 以及对科学细节的关注, 首先是提出了或想要提出一种政治性的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观点。迪尔克(Dilke)女士, 一位重要的自由派政治家和出版人的妻子, 要求自己死后被火化——作为“一个科学实验”。当时英国还没有一个地方能这样做; 于是她的遗体被运送到德国哥达(Gotha), 在一群应邀而来的观众面前, 她的遗体在一种改良设计的西门子焚化炉中被火化。根据她(生前)的要求, 其尸体的燃烧过程每分钟都被详细地记录, (实验)结果最后被发表出来——包含着所有耀眼可怕的细节。⑤
所有这些基于证据的关乎公共健康、生态和能源效率的论说, 并没有令火葬反对者心悦诚服。在火葬反对者看来, 这种谈论死者的方式远不止于效益, 换言之, 基于效益的种种论说, 普遍都不仅仅是关于效益。批评者指出:火葬论者所对付的真正问题是, 抹去历史、情感和美学, 转而偏向自然主义和工具性。有人致信《里士满和特威克汉姆时报》 (The Richmond and Twickenham Times)写道:“令人怨恨的正是亨利·汤普森的效益主义。”另一份报纸问道:“人的头发难道不能被转化成什么具有公共效益的东西?”“父母对孩子的爱消失了, ”格洛斯特当地的一份报纸(The Gloucester Mercury)哀叹道, “效益主义者很快将矫正我们的思想, 抹去我们过去所有的愚蠢行为。”①汤普森等人的论说剥夺了死者的一切, 只剩下他们的生物属性。
“古老的柴堆是诗意的, 而现代火葬的历史则是犬儒的(cynical)。”意大利著名卫生学家和人类学家保罗·曼特嘉莎(Paolo Mantegazza)的这句话包含了尴尬的感情转变。所有“杰出的化学家, 有创造性的建筑师, 以及热情的人道主义者”都只是在说“卫生问题, 而无人论及情感”。反对者被迫需要为他们“对心灵和宗教的诉求”寻找借口、请求宽恕, 而其实, 如何对待死者尸体, 完全是情感问题, 而非卫生问题。换言之, 火葬将亡者推向了生硬的、过度理性的现代性一边。②
火葬与进步一般而言, 火葬是站在进步主义一边的, 但多少带着一些严格且好战性的主张。格林童话的收集者之一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在他于柏林研究院所作的学术演讲中指出:火葬在前古典时期的古代出现, 代表了人类在精神培养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对火的运用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 在宗教领域体现于灵魂上天、肉体入地, 以及燃烧献祭; 它也是实用的——骨灰易于运送; 它还是理性的——火(消耗尸体)更快, 土(消耗尸体)则慢。③
英国某位火葬论者指出, 那些依旧偏爱土葬的人可能只是盲目受着习俗的驱使。还有什么其他理由, 可以解释为何有人愿意将他们所爱之人葬于潮湿的泥土里, 与蠕虫及来自其他坟墓的渗漏物埋在一起?病态的习惯——土葬就是其中之一——“属于无理性一类”, 其存在只是为了“受到批评和颠覆”。但尤其在英国, 有一种温和态度, 会“温柔对待”那些相信珍爱的亡者能完好入土并“迷恋于这个盲目幻觉”的人。然而, 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④
美国世俗论者奥古斯丁·科布(Augustine Cobb)发现土葬历史受到愚昧文人的严重控制, 并明确表示基督教历史与死亡历史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通过巧妙的管理, (坟墓)变成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的连接物, 并成为一种最有力的要素, 为教会所持有, 用以掌控信徒。”科布认为, 这一点在18世纪对基督教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作《罗马帝国的衰亡》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本伟大的书中, 吉本嘲讽了晚期帝国君主、将军和执政官出于“迷信的敬畏”, “虔诚地敬拜一个帐篷制造者和一个渔夫的坟墓”。1920年的德国, 当一些更严重的事情迫在眉睫时, 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一场小型辩论, 关于火葬协会的成员是否有责任将他们的孩子转学, 放弃公立学校的宗教指导。共产党人认为“是的”, 因为文化革命是最为危急之事, 必须彻底进行。1926年, 革命的俄国火葬协会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界定为“好战的无神论者”。⑤
火葬的进步性或明确的现代品格, 并不一定伴随着反宗教(irreligion), 只是在现代性产生世俗化的那种最普遍的怀疑感中, 才蒙上反宗教的色彩。在此并不存在关于火葬的神学或犹太法学的观念。现代火葬出现于旧政体崩塌之时, 孕生出一种特定的、偶然的环境条件, 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 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火葬反对者纷纷形成。
火葬、革命政治和反宗教不可否认, 是法国大革命复活了远古的火化实践, 即便这种说法很笼统。1791年, 伟大的教会批评者伏尔泰的骨灰——装在一个古典的骨灰盒中——由异教徒的队伍捧着, 进入先贤祠安放。1797年11月11日, 火葬作为土葬的一种替代方式被法律确定下来; 但到了1804年, 在教皇庇护七世与拿破仑的协议中又被定为非法。而问题关键并不是关于火葬(相对土葬)社会后果的某种特定看法。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这位法国大革命的剧作家、科幻小说之父, 以及卢梭的热情追随者, 凭借许多美学的和政治的理由反对火葬, 这些理由中有一条是, 由于个人可以将去世的祖父和叔叔的骨灰盒放在家中的橱柜里, 使得私人祭坛(private sepulcher)成为可能, 而这是对“社会安宁与祥和的公然侮辱”。与此相反, 意大利人认为法国人把自己亲属的骨灰置于家中的经验会“对个人道德施以一种非常健康的影响”, 并构成一种“家庭的圣所, 这正是社会秩序的永恒基础……无可争议的是, 人们的家族世系将成为道德再生的一个重要元素”。实际上, 火葬还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毋庸置疑的一点在于, 将死者从教会的神圣土地下夺出, 摆脱神职人员的掌管, 是整个事业的核心。①
在每一个西方国家, 火葬都是一项左翼的事业, 但教会与火葬倡导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中各不相同。在英国, 教会与火葬倡导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相关的, 反教权主义和反宗教势力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几乎没有影响。而在德国, 情况截然相反, 工人阶级运动是地方火葬协会的主力, 路德教派的火葬反对者所针对的就是火葬与社会主义的结盟。
在意大利, 情况最清楚, 进步的和现代性的力量, 以及反教权主义势力——共济会会员、卫生学家、世俗共和主义者、各类民族主义者、北方人——都拥护火葬。焚烧死者是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而教会转而将这一切视为意大利统一的错误象征, 当教会1886年正式谴责火葬时, 其理据不是神学的而是社会的、美学的和政治的。火葬倡导者怎么也不会隐瞒这样一个事实, 即火葬仪式的开创性就在于它的非教会性质, 其现代性就表现在反教权主义、“科学性”, 以及立足于民间社会。共济会是这一切的代表, 而教会从一开始就将火葬的整个事业解释为共济会的一个阴谋。1908年, 《天主教百科全书》 (Catholic Encyclopedia)的作者总结道:火葬就是“关于反宗教和唯物主义的一种公开宣称”。他切中了要点。
意大利统一战争的人民领袖加里波第(Garibaldi)在其公开的遗嘱中想要表明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要求自己的遗体被火化, 认为面对这样的死亡, 神职者的种种邪恶阴谋都将无计可施。显然, 加里波第希望自己这个引人注目的遗愿——以旧式异教徒的方式在木柴堆上燃烧, 作为对教会的最后一次攻击。然而(1888年以前火葬在意大利是非法的, 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 没有人去执行加里波第的遗愿, 因为如果这样做, 则表示故意对抗教会, 而且也将代表这位英雄要在死后拒绝履行最后一次公职服务, 如此就意味着冒犯——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惹恼了——所有人。即使是火葬协会, 也不会支持那位年轻的寡妇去完成她丈夫的遗愿。加里波第在民间的盛大葬礼中入土。但是, 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 要点在于他以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个选择。②
火葬与个人主义火葬反对者的一个最常见的抱怨是, 火葬象征着一种危险而猖獗的个人主义。而火葬的一个吸引力也在于, 它使安置死者成为一件私人的事情, 它营造了一种场合, 用来对生者的世界做最后的、有力的文化干预。英国有一个疯狂的威尔士人, 力图在英国使火葬合法化。他名叫威廉·普莱斯(William Price), 被《威尔士名人录》 (The Dictionary of Welsh Biography)收入在“古怪之人”条目之下。普莱斯认为“死亡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 声称自己已经活了一万年, 为(科学论者未能完成的)火葬合法化而斗争, 这其实是这位新德鲁伊教派信徒的“一些奇异的花招”。或者更准确地说, 一位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根据普通法对该威尔士人的花招所作的判决, 推倒了火葬完全合法化的法律壁垒。
1884年1月18日, 普莱斯把他死去的儿子——带着挑衅意味地给他取名为耶稣·格里斯特(Jesu Grist)——带到兰特里森特(Llantrisant)格拉摩根希尔镇附近的一个农田, 向遗体做了德鲁伊教派的祷告, 将其放入一个装满石蜡油的桶中, 然后火化, 就像古代凯尔特人的习俗一样。普莱斯因此被捕, 后又被释放, 一个验尸官的陪审团为其辩护。3月21日, 他再一次用半吨重的煤炭火化了自己另一个儿子(婴儿)的尸体。他又遭到逮捕, 在最高法院受审。法官斯蒂芬森(Stephens)宣布如下判决:“一个实施火葬而非土葬的人, 并不构成犯罪, 除非他的方式在法律上妨害公众权益”; 而普莱斯在公共场所火化耶稣·格里斯特的尸体不符合妨害公众的标准, 对其的指控不成立。火葬, 虽然尚未完全合法, 但无论如何都不是非法的了。普莱斯惹恼了邻居, 却被无罪释放。①
通过火葬想象死亡火化尸体的显著特征是:对于尸体在化为原子之后会变成什么提供了几乎无穷尽的想象可能。例如, 在英国, 通神论(Theosophy)奠基人布拉瓦茨基(Blavatsky)夫人的遗体在沃金火化之后, 骨灰被撒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 以重新进入宇宙循环。在克罗登(Croydon)自由基督教堂的首席女低音艾丽丝·邓(Alice Dunn)的火葬仪式上, 一位新斯韦登伯格派的有灵论者、著名的自由无宗派传教士胡普斯(J. Pages Hoops)宣扬, “尸体脱离凡尘”。他欢迎这样的时刻来临, 即没有任何纪念物或场所与死者相连, 而唯一“合适的圣祠”就是“爱的精神”。
火葬没有提供多少字面意义上的“卫生”, 而是抹去死者尸体的一种原始污秽。“更为美好的是, 可怜的尸体, 经过净化之后, 应该被释放到阳光之中。”对尸体本身而言, 火就像一场“夏日玫瑰的芬芳沐浴”, 与土葬的“玷污”作用形成天壤之别。由于上帝不是物质的, 在他看来, 对于死者的复活, 精神意义上的火葬而非身体意义上的火葬, 才提供了一条迅捷而合适的想象途径, 得以使灵魂释放, 升入天堂。②
名字、身体、处所和记忆之间的古老链接似乎濒临断裂, 尽管还有些时日。火葬协会主席在1945年指出, 我们可以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 即有一天我们只要简单地把死者的骨灰撒在花园里, “用一棵树或一丛灌木作为‘标记’, 用一块不醒目的石碑刻上他的名字”。有着圆柱和柱廊的骨灰安置所, 当然还有墓地, 很快都会成为过去(其实并没有那么快。③例如, 19世纪位于汉堡的欧兹道夫墓地只是到最近才成为一块自然的田野, 供人们分撒骨灰, 与他人的骨灰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 大多数骨灰还是被掩埋的。根据新《名人录》 (DNB)的传记, 1945年以前去世并被火化的112人中, 骨灰因各种原因未被掩埋的只有6人(5%), 这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布拉瓦茨基夫人;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骨灰或许被混进他所居住的新墨西哥农场的一座所谓礼拜堂的建筑材料里, 也可能在法国凡斯(Vence)的里维埃拉镇火化之后被撒进了地中海; 皇家航空的兼职主席理查德·格迪斯(Richard Geddes)先生的骨灰由一架公司飞机运送, 于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上空撒下。至于其他人, 他们的骨灰被放在骨灰盒里, 有意要带有一些历史关联, 然后掩埋在传统的场所或者新的骨灰安置所, 也可以被存在教会墓地中靠近土葬尸体的地方。
泌尿科医生和英国火葬协会的创始人亨利·汤普森——因其在皇家学院的展览而被誉为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发表了以经典模型为基础的个人设计。伊特鲁里亚模型已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作为倡导火葬的文献的图解说明。简而言之, (想象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1945年以后, 《名人录》中有152位名人是火葬的, 其中33人的骨灰被分撒, 占22%)。
回到开始20世纪末期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被问起, 是否存在一种社会意义的基础——一种在本体论上优先的类别的符号学基础——用以阐明意义?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的解释, 他说“一路往下都还是乌龟”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①
我的主张是, 要通过阐明一组组关系及其发展来解释现代火葬的出现, 这些关系是话语性的和实践性的。这个问题在与种种关系中呈现出不同层面的意义。这种阐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正如文学批评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所发现的, 在揭开一个隐喻的最后, 总是会以“等等”来结尾。对隐喻意义和死亡仪式之意义的阐释都是不可能穷尽的。②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头大象比其它大象更为根本。一如我曾说, 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死亡更强有力地有助于意义的创造。为什么说“死亡的神圣性”——这个用语属于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辛(Lessing)的用语?为什么死亡对于文化构建和运作如此重要?我将给出五个理由, 以此作为结论。
为什么死亡如此重要首先, 死亡进入文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原初时刻。关于死亡的知识立足于我们这个物种存在的开端, 或者说, 它让我们进入完整的人性, 这是一种老生常谈, 也是确真的。任何一种宇宙观都有关于生前死后的类似叙事:死亡的来临; 背离上帝或诸神; 最终以某种方式战胜死亡。现代动物行为学肯定了这种最为深刻的神话母题。甚至是查尔斯·达尔文也在其论证人类和动物之间情感连续性的著作中指出, 在亲缘关系上离我们最近的动物猴子不会哭泣, 在这个意义上说, 它又是离我们很远的。
因此, 死亡形态学既是人类活动的一般标志, 又是人类一种特定工作的方式。从这个事实出发, 我提出死亡的第二个意义, 即死亡作为文明创造的意义:让死者安息的实践活动——安置、哀悼和纪念他们——是根本性的。18世纪思辨性历史人类学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维柯(Gianbattista Vico)认为, 埋葬死者是生成和维系市民社会的三种“普世的人性体制” (universal institutions of humanity), 另外两种“普世体制”是婚姻和宗教, 而它们都将很快地回归到死亡体制中。生者处于已故祖先和他们自己的后代之间; 这是最原初的律法(lex)——谱系的法律——将家庭或氏族造就为一种体制, 联结着未出生的人和已故者, 并把它投射到历史事件之中。正是家庭或氏族要为适当照料死者负责。死亡与宗教的关系是如此奇异地被制造出来, 以至于它们的密切关系自古以来就已是自明的了。西塞罗(Cicero)在关于宗教的“论法律”一节中论及如何对待死者:坟墓变成宗教崇拜的场所。我可以提醒大家的是, 基督教反对古代地中海世界有关死者污染的禁忌, 尔后他们将尸体迁至教堂安置, 这代表了异教世界衰落的一个最显著的分水岭。③
从维柯的观察中, 可以得出死亡作业的第三个意义:对死者的处理是具有规范意义的。一种文化上特定的、适当的安葬是成为文明的标志, 而对死者的不敬等同于野蛮——正如人文主义者阿尔伯蒂(Alberti)指涉如今许多对待尸体的做法:“很少有人会野蛮到不使用坟墓的地步, 除了那些印度偏僻地区的食鱼野人。”他告诉我们, 他们只是将死者抛入海中, 声称尸体总是要消散的, 无论消散在空气中、火中、水中还是土壤中, 并无任何差别。如何对待死亡, 成为划分野蛮与文明、残暴与体面的界限标准。
公元前5世纪, 希罗多德(Herodotus)已经理解了这种规范性的作用。而他也是最先理解这种规范作用会具有怎样的文化特定性。人们自身关于死亡的习俗是不可化约地正当的, 在伦理上又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 我们也认识到, 其他持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人们同等地珍视自己关于死亡的习俗。当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 (在一项小小的社会科学实验中)向印度人提议火化尸体时, 印度人震惊得难以名状; 而希腊人则惊呼,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在父亲死后吃掉他们的父亲”, 就像印度人所做的那样。希罗多德总结说:“所以, 这些事是由习惯做法建立的, 我认为, 这就像品达(Pindar)在其诗歌中写到的, ‘所有事中, 律法为王。’”换言之, 如何安置死者既是根本性的——“除了疯子, 没有人把这类事当儿戏”——同时又是习俗性的:律法的问题。①
亡者的作业在文明创造中还有第四个意义:死亡作业拥有——或者不如说, 它们已经被当作——一种本质的典型, 用以界定一个文明的特征。死亡一直是一种绝佳的举隅法(或曰提喻法, 一种以局部代表整体或以整体代表局部、以特殊代表一般或一般代表特殊的修辞手法)。雅典战争马拉松阵亡者的坟墩在古代已经是一个划时代的场景, 是西方战胜东方帝国的标志。八个多世纪后, 罗马旅行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前去拜访这一坟墩。两千多年后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 当林肯为第一个美国国家公墓献辞的时候, 他懂得自己的使命是要将民主雅典和围困的盟军联系起来, 而他的方式就是阐明这两个典范性亡者墓地之间的密切关系。林肯非常实际地明白, 一个公墓何以能成为一个国家重生的景观。②
最后, 还有一个意义是, 死亡——作为既存的事实, 我们哀悼丧失, 似乎如此不可思议, 以至于产生了如此极端的变化, 这种变化发生在身体内部, 发生在身体及其昔日活动之间的关系中等等, 并通过一系列其他事实——表征着或被用以表征关于人类状况的某种终极真相。亡者的作业是要宣告如此终极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格拉底说, 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为死亡做准备。
我已经提出, 火葬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出现, 不是某种预先发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需求的结果; 它没有以一般的方式“反映出”某种新的现实——诸如土地匮乏、公共卫生的需求、或“世俗化”。它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的, 是通过主张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安置死者, 而使得一种政治性的和广义上文化性的规划在竞争中获得了文化权威。火葬打开了一系列新的方式来思考死亡, 以及许多通过死亡问题来进行思考的方式。一种新的安置技术——或者准确地说, 一种旧的安置技术经大大改良后被重新采纳——开辟出许多惊人广泛的路径, 由此死者得以创造文明, 生者得以让死者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