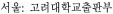《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的系年始自公元前18年,然而中国正史为百济国立传始自成书于南齐永明六年(488年)的《宋书》,此后《南齐书》、《魏书》亦为之作传。在《三国志·东夷传》中记马韩五十余国中有“伯济国”,《后汉书·东夷传》特意指出三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后汉书》成书于5世纪,此时百济已经与晋、宋王朝往来密切,范晔此书法恐寄意暗指伯济与百济间的历史联系。然而,关于“伯济”与“百济”的关系,现代史学家的看法莫衷一是。①无论如何,百济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政治实体直接与中央朝廷发生联系,是在四世纪以后,而这显然与四世纪初乐浪、带方二郡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崩溃有关。②
4世纪初,大一统的局面随着西晋王朝的瓦解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秦汉以来大一统所塑造的“天下意识”仍然是凝聚人心、约束政治行为、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元叙事。作为新兴政治实体的百济,它也无法脱离当日的“政治正确性”。百济的天下意识及其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参与,不仅对百济自身的国家建构影响甚巨,而且成为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对该问题的梳理,也是对4—6世纪“天下”政治形态的一种类型学描述。
一 百济的初次朝贡与东晋授官的由来百济第一次与东晋发生联系是在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正月,近肖古王(346—375年在位)遣使朝贡。次年六月,东晋朝廷“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③关于此次百济与东晋往来的具体内容,史言不详。但是百济王初次遣使朝贡便被拜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值得探究。
咸康二年(336年),高句丽曾向东晋“遣使贡方物”,④建元元年(343年),高句丽再次遣使朝贡。⑤高句丽两次出使均无晋使回访,亦未获得任何官职。再对比同处东北的慕容氏。晋愍帝建兴中,慕容廆被授予“镇军将军”号,这是对其此前平定平素连、木津之乱的酬劳。①而百济无功于晋却获“镇东将军”号,就更显得双方首次交往便如此信任的不同寻常。
如果从近因来看,百济这次遣使的背景是369年败高句丽于雉壤、371年连败高句丽于浿水、平壤,杀故国原王、夺南平壤。②遣使入晋,有向东晋献捷的意图。从东晋的立场上看,自永和八年(352年)慕容氏称帝,东晋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力。虽然“天下”观念仍然主导着当时的东北政局,但是,这个“天下”已不是专属于晋室的天下,而有可能是慕容氏的天下,前燕称帝后,“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③高句丽成为前燕所主导的“天下”之成员。二十年后,百济的遣使朝贡,为东晋天下共主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370年,前秦灭前燕,统一华北,其势如日中天,苻坚有一统天下之志。东晋无论从实力上看,还是从天下认同上看,形势都岌岌可危。百济的朝贡无疑是对东晋的支持。从东晋内部的情况看,咸安元年(371年),桓温排斥并诛杀以前执政的殷氏、庾氏。百济的朝贡也有利于维系东晋朝延的体面。
为何与中原王朝素无关系的百济突然会在372年朝贡,为何百济近肖古王不向前秦朝贡,而向东晋朝贡。这可能与夫余有关系。一百年后,即472年,盖卤王(455—475年在位)遣使朝魏,所上的表文中明确写道:“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④关于“源出夫余”及百济的建国,众说纷纭,李丙焘、白鸟库吉,今西龙,稻页岩吉,末松保和,K.J.H. Gardiner, Gari K.Ledyard都有重要的论述,大多承认夫余对汉城百济的影响,区别是,一说认为夫余人来后百济王权更迭仍发生在王室支属间,另一说则认为夫余人的到来造成百济统治阶层的变更。⑤近肖古王的夫余族裔身份是极有可能的。尤其是近肖古王元年即夫余为慕容氏所灭的346年。538年圣王迁都泗沘后又改国号为“南夫余”,这一称谓与346年后重建的“东夫余”、“夫余”相对。⑥这些都指向百济王族“源出夫余”的史实。在汉、魏、西晋的东北政局中,夫余是除郡县以外的又一重要支持力量。
自公元21年高句丽大武神王伐夫余后,夫余在与高句丽的对抗中处于弱势。⑦永宁元年(120年)夫余王遣子诣阙贡献,随后东汉与夫余在东北联合军事行动。建光元年(121年)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延光元年(122年)春二月,夫余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⑧以后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王亲自来朝。除桓帝永康四年(170年)寇玄菟外,桓帝延熹四年(161年)、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又两次遣使朝贡。汉末公孙度霸辽东,与夫余王尉仇台为姻亲。曹魏正始中,幽州刺史毌兵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夫余供军粮。⑨
太康六年(285年),夫余为慕容氏所灭,夫余王依虑自杀。晋武帝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⑩以此罪免东夷校尉鲜于婴,改任何龛,督邮贾沈败慕容氏,帮助夫余复国。这是晋武帝以其国力维系天下秩序。
这件事影响非常大,慕容氏由此定下“世奉中国”、“不与晋竞”的自我定位。①同样,这件事对于夫余后裔也会留有重要影响。作为夫余后裔的百济王室在击败高句丽后仅三个月,其使者便到达建康,考虑到路途时间,或许战胜高句丽后立即就已派遣使者。这反映了百济的天下意识,它并非是无拘无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很难想像一个从未向都城宫阙朝贡的国家会突然派遣使者,只有从历史渊源才能解释百济的遣使,以及百济倒向东晋而非如日中天的前秦。这种历史渊源极有可能是百济的“天下”意识的根基。
总而言之,从近肖古王开始,百济自觉地成为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有机部分。②尤其是慕容氏称帝后,百济成为东晋南朝的东北战略支点。这从近肖古王“领乐浪太守”的官职上也可看出。东晋不仅承认百济对汉魏晋以来朝鲜半岛上最重要的乐浪郡故地的领有,同时将其视为官僚体系中之一环。
二 南朝对百济王的授官及百济在天下秩序中的位置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夏四月,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③这应该是册命新的百济王。此前太元九年(384年)秋七月,枕流王(384年—385年在位)曾遣使贡献方物。④这应是对383年淝水之战东晋胜利的祝捷,也是向东晋通报百济王位继承的变动。东晋对百济王位继承的册封,表明东晋对其天下诸国的干预。是东晋国力扩张的结果。
辰斯王(385—392年在位)、阿莘王(392—405年在位)时代与高句丽对战,百济逐步转弱。史籍上缺乏这两代百济王的朝贡记录。高句丽反而重新转向东晋的“天下”。“高句骊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⑤这是东晋第一次册封高句丽,而这一官号本由前燕授予高句丽王高钊,现由东晋赐予高句丽王高琏,只是去“征东大将军”为“征东将军”。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承认乐浪为高句丽占有,故承认高句丽王为乐浪公。
腆支王(405年—420年在位)在阿莘王死后的内乱中即位,在内忧外患中,百济于次年(406年)立即遣使赴晋朝贡,有可能是请求册封,以东晋授官的合法性来稳定百济国内政局。义熙十二年(416年),东晋朝廷“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其官职与余晖完全相同,更说明了百济王权继承在东晋政治体系中的稳定性。之所以直到义熙十二年才册封,是因为东晋在同年收复洛阳,朝廷加刘裕宋公、备九锡。如同淝水之战后册封百济一样,这是东晋国力扩张的结果,也与372年册封百济一样,是东晋权臣政治地位上升的结果。
从余句、余晖、余映三代的册封来看,东晋—百济的关系既建立在国际形势的变动上(东晋国力增强或百济国力增强),也建立在各自国内的政治需求上。这种依存关系的前提是“天下意识”,而这种依存的结果是强化了彼此共同的“天下”观念,并融入到同一个天下秩序中。
对百济王的册封成为南朝嬗代过程中的惯常模式。晋、宋嬗代发生的永初元年(420年)七月,“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⑥然而腆支王余映已经于当年三月死,显然,这次“进号”并非百济所求,而是晋宋嬗代时,刘裕以“进号”的方式试图获得其“天下”中各方势力的支持。宋武帝诏书:
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映,并执义海外,远修贡职。惟新告始,宜荷国休,琏可征东大将军,映可镇东大将军。持节、都督、王、公如故。①
又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三《外臣部八封册第一》,南齐始建,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诏:
宝命惟新,泽波绝域,牟都世藩东表,守职遐外,可即授,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
也是在强调“宝命惟新”。齐、梁嬗代,梁武帝天监元年,诏“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 ②陈朝的册封稍晚,为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③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朝对百济王的授官是有继承性且稳定的,所升者为将军号的品秩。
从百济的角度考察,自久而莘王(420—427年在位)之后的历代百济王大多在即位之初便遣使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这成为百济惯例。下文试言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百济王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这既是对晋宋易代百济王进号的回应,也是请求对久而莘王的除授。元嘉二年(425年),宋文帝诏百济:
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効诚,远王纂戎,聿修先业,慕义既彰,厥怀赤款,浮桴骊水,献賝执贽,故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勉勗所莅,无坠前踪。今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④
从文意来看,“嗣位方任”、“聿修先业”、“勉勗所莅”,都表现诏书是写给新即位的百济王即久而莘王的。“其后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
毗有王(427—455年在位)四年,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以映爵号授之”。⑤
盖卤王(455—475年在位)三年,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遣使求除授,诏许”,⑥ “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⑦
文周王(475—477年在位)、三斤王(477—479年在位)处于汉城百济覆灭之后,人名、时间史料记载可辨析之处甚多。上引《册府元龟》记年为南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牟都授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但《三国史记》对应该年为东城王三年。李基东拟定牟都即文周王。⑧
按《南齐书·东夷传》,东城王(牟大,479—501年在位),“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使兼谒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曰:“‘惟尔世袭忠懃,诚着遐表,沧路肃澄,要贡无替。式循彝典,用纂显命。往钦哉!其敬膺休业,可不慎欤!制诏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牟大今以大袭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⑨按《梁书》,应该是在永明中。⑩
武宁王(501—523年在位)二十一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其年,高祖诏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藩海外,远脩贡职,廼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⑪
圣王(523—554年在位)元年,梁武帝普通五年(523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①
威德王(554年—598年在位)九年,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②
从《百济武宁王志石》“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的自述来看,百济方面是认同南朝对百济王的官职除授与王爵封册的。从上述南朝所授官号来看,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位置是稳定的。
据《宋书》卷九七《东夷倭国传》,刘宋时,倭王珍“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倭王武“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试图通过刘宋朝廷的授命,将百济纳入其都督范围。但是对倭王珍,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只是在元嘉二十八年,加倭王济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仍然不将百济置于倭国的都督之下。对于倭王武试图都督七国,刘宋朝廷仍然只同意都督六国,将百济排除在外。此时已经是顺帝升明二年(477年),此年为萧道成执政的头一年。可见,宋齐统治者都将百济视为其天下秩序中的重要一环,绝不可能由倭国来都督百济诸军事。
而且从所除将军号来看,倭国所受将军号为“安东将军”,为三品,直到顺帝时代萧道成执政、寓意“宝命惟新”才升为二品的“安东大将军”。而百济自建宋以来,一直是二品“镇东大将军”。而且在二品的序列中,“安”低于“镇”。可见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三 百济“内属”与南朝对百济内部权力建构的参与从毗有王(427—455年在位)开始,百济与南朝的关系具有新的特征。盖卤王(455—475年在位)时代,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余庆遣使上表曰:‘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乂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③
在宋官品中,冠军将军、征虏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均为三品,宁朔将军、建武将军均为四品。余庆本人为镇东大将军,第二品。上述诸人以余姓为多,这种赐除,显然是以刘宋职官体制来构建百济内部的权力秩序。其结果无疑进一步提高刘宋朝廷在百济国内的威望,进一步强化其“天下意识”。
这一做法在汉城百济崩溃后,熊津百济重建的过程中,再一次使用。《南齐书》卷五八《东夷传》:
报功劳勤,实存名烈。假行宁朔将军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国难,志勇果毅,等威名将,可谓扞城,固蕃社稷,论功料勤,宜在甄显。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宁朔将军、面中王姐瑾,历赞时务,武功并列,今假行冠军将军、都将军、都汉王。建威将军、八中侯余古,弱冠辅佐,忠効夙着,今假行宁朔将军、阿错王。建威将军余历,忠款有素,文武列显,今假行龙骧将军、迈卢王。广武将军余固,忠効时务,光宣国政,今假行建威将军、弗斯侯……
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参军臣会迈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着。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寻其至効,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且玄泽灵休,万里所企,况亲趾天庭,乃不蒙赖。伏愿天监特愍除正。达边効夙着,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务不废,今假行建威将军、广陵太守。(万)[迈]执志周密,屡致勤効,今假行广武将军、清河太守。”诏可,并赐军号,除太守。①
前一段有脱文,从后一段“牟大又表曰”看,应该也是牟大向南齐朝廷的奏表。这两次奏表都在于请求为百济国内臣僚寻求除授。而且文中多次提到“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在东城王(479—501年在位)时代,任命百济官僚,先有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已经是惯例了。
与盖卤王时代多“余”姓相比,此次异姓为多,当是熊津百济重建过程中需寻求多方支持而出现的现象。从官职上看,除了宁朔将军、冠军将军、建威将军、龙骧将军、广武将军、宣威将军等将军号外,广阳太守、朝鲜太守、带方太守、广陵太守、清河太守等地方职官也出现,这些地方官职并非是百济国的地方官府,而是朝廷的地方官府。
《三国史记》卷二六《百济本纪第四》:
东城王六年(484年)春二月,王闻南齐祖道成册高句丽巨琏为骠骑大将军,遣使上表请内属,许之。
上引《南齐书·东夷传》所载,当是这次“内属”的结果。而且出任太守的高达、杨茂、会迈三人,都曾出使刘宋与南齐,“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使臣因与朝廷交往,为朝廷所了解,故出任朝廷所任命的官职,这些是宋齐以来的传统。《南齐书·东夷传》还记载建武二年(495年)前百济打败北魏事。牟大两次上表要求南齐朝廷对有功将领及文官除正:
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皇,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今邦宇谧静,实名等之略,寻其功勋,宜在褒显。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赞首流为行安国将军、辟中王,解礼昆为行武威将军、弗中侯,木干那前有军功,又拔台舫,为行广威将军、面中侯。伏愿天恩特愍听除。
又表曰:
臣所遣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兼长史臣慕遗,行建武将军、城阳太守兼司马臣王茂,兼参军、行振武将军、朝鲜太守臣张塞,行扬武将军陈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务,见危授命,蹈难弗顾。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
第一份表文中“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是表明上一次对姐瑾等人授官的效果,南齐朝廷获得他们的拥护。第二份表文中“在官忘私,唯公是务”,则表明百济对官位的“公”的性质的理解。可见,至少在熊津百济东城王牟大统治时代,由南齐朝廷除授百济官僚不仅是常例,而且其合法性还建立在对职官职事“公”的性质理解基础上。正是这一理解,使得百济与南朝在政治世界中有了共通的可能性。
再如圣王(523—554年在位)时代,“又于大通元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②大通为梁武帝的年号,百济圣王为梁武帝创立佛寺,这也是“内属”的表现。据Jonathan W. Best研究,圣王十八年(538年)迁都泗沘,便是为了选择与中国外交、商业、文化往来更加便利的都城地点,反而将军事防御因素的权重降低。③
四 百济与南朝共享同一文化世界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中的特殊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官品序列中,更重要的是分享东晋南朝的文化世界。
(元嘉)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①
《易林》、《式占》均为卜式类书。《隋书》卷三四《经籍三》子部五行类,有《易林》十六卷,焦赣撰;《易林》二卷,费直撰;《易林》三卷,鲁洪度撰。腰弩则为当日先进的军事装备,为南朝皇帝侍卫的装备,梁武帝时值宫门的四十九队中便有“腰弩”一队。②余毗所求皆为应用性的知识与技术,此时为汉城百济后期。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③
这是在泗沘时期。南朝与百济在物质文化即技术上的分享,以为越来越多的出土实物所证实,④武宁王墓即其显证。⑤与今人的想象完全不同,南朝对于文化传播是持保守态度的。
清光绪末年山东省景州出土《李璧墓志》言及:“昔晋人失驭,群书南迁。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为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⑥此事又见于《南齐书》:“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事竟不行。”⑦南齐朝廷拒绝了北魏孝文帝借书的请求。
再如永明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弥承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祕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⑧
百济在元嘉二十七年所获得的《易林》、《式占》、腰弩,正是宕昌王所求的军仪及伎杂书,齐明帝诏书严禁向宕昌流传的军器、内伎,却早已被宋文帝大方地送给了百济。
吐谷浑拾寅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⑨
宕昌王、河南王的官衔多于百济王,其官品也与百济略微对等,然而,无论是出身于羌人的宕昌王,还是出身于鲜卑的河南王,都无法获得其想要的文化、技术。牟发松先生认为,不予借书,是南朝制度上的硬性要求。⑩可见,宕昌王、河南王并非受到南朝朝廷的歧视,而是百济受到了非同寻常的优待。在历史记录上,没有出现过百济所请被南朝拒绝的情况。
因此,百济与东晋南朝之间,应该已经超越单纯政治、经济利益的交往层面,而深入到文化共同体,乃至情感共同体之上。《梁书》卷五四《东夷百济传》记载侯景之乱中百济使者的表现:
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梁书·侯景传》中还专门强调百济使者“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①“号恸涕泣”乃是对当日文明世界之荒毁的痛惜。
五 百济与东晋南朝的连环盛衰事情的另一面是,百济与东晋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镶嵌与同构,也使得它与江左王朝的政局同起同落。汉城百济的崩溃是在盖卤王二十一年(475年)。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八月丙辰,“百济国遣使奉表请师伐高丽”。②这是百济有史以来第一次遣使北朝。在表文中,余庆:“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百济自感处于亡国之机,首次遣使便贸然请求北魏征伐高句丽,指责高句丽“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脣齿,谋陵王略”。③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刘宋明帝泰始二年(466)薛安都降魏,到泰始五年(469年)沈文秀被俘,刘宋丧失了青、冀、兖、徐和豫州的淮西,这是刘宋与百济海上交往的主要通道。刘宋的衰落,以及百济面对高句丽的颓势,使得百济转而向北魏求助。表文中“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似乎是在唤起冯太后对于高句丽杀北燕王冯弘的记忆。
北魏的绥靖政策最终使汉城百济于三年后覆灭。重建的熊津百济则再次倒向南齐。“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南齐书》将上述记载记在建武二年(495年)牟大遣使上表之前。何德章先生认为此事为百济缪说,建武元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北魏、南齐闹翻,南北朝开始了几十年的战争。百济于次年上表,其意正表明与南齐同仇敌忾。④这是百济对外政策随南朝形势而变的显例。
如上引Jonathan W. Best的观点,大同四年(538年)百济自熊津迁都泗沘,是为了与江左王朝更好地往来。此时是梁朝的发展顶峰。同样,太清二年(548年)爆发的侯景之乱使得南朝衰落,如上引所示,为百济使者所亲见。552年侯景之乱才被平定,百济使者方能归国。554年,百济圣王在与新罗的战争中被杀,“诸军乘胜大克之,斩佐平四人,士卒二万九千六百人,匹马无反者”。⑤百济再次受挫。百济的盛衰与东晋南朝盛衰之间有着甚为显著的对应性。
4世纪初叶西晋大一统瓦解之时,以往长期生活在以郡县为主的体制中的各族,纷纷开始走上建立政权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与在黄河流域及四川盆地的十六国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百济的选择并非是脱离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或争当天下中心,而是选择与东晋南朝在同一“天下意识”下、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从而在国势的盛衰上也与之相应。这在东晋南朝的“天下”中是独一无二的。而在此后的历史中,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的先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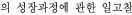

 對中國郡縣關係一考察》,《傳統文化研究》第4卷,1996年,第153—183页;宋知娟:《帶方郡
對中國郡縣關係一考察》,《傳統文化研究》第4卷,1996年,第153—183页;宋知娟:《帶方郡 研究》,《史學研究》第74卷,2004年,第1—26页。
研究》,《史學研究》第74卷,2004年,第1—26页。

 :一潮閣,1996年,第152—156页。
:一潮閣,1996年,第152—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