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问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出版不久,即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后于1851年传播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①此后,《共产党宣言》先后被译成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和意大利文出版。1881年至1891年间,日本学者不断著书立说,介绍《共产党宣言》。1904年,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共同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刊发在《平民新闻》第53号上。② 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全文刊登了《共产党宣言》。③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被誉为“红色中华第一书”,④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清末以来,中国报刊便不断登载《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并引发了社会关注。1920年夏,陈望道翻译的中文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在此过程中,以出版为核心的现代传媒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媒介形态变迁中的《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清末,伴随着西方宗教刊物在中国的出现,谷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并支撑和推动着外国在华报刊的出版活动。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报刊的出现,给国人带来了更丰富的阅读材料和阅读体验,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并刺激其中的先觉者创办刊物。《申报》的成功,不仅充分展示了现代印刷技术的魅力,还展示了新式书刊在传递信息、影响社会和获取利润方面的巨大优势。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刺激了国人的变革愿望。中国人开始重视现代报刊,并创办各种刊物。现代印刷也从官办书局、教会团体等机构中走出,走向民间。维新变法之后,民间自办的刊物大量出现。它们的言论主张,甚至办报本身,都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些报纸上的公开讨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无论是国内的刊物还是海外的报刊,都在享受着新式传媒的恩泽。在这股传媒变迁的潮流中,《共产党宣言》也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
开《共产党宣言》译介先河者,当属《万国公报》。188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由周刊改为月刊,开始刊登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该报于1899年的第121册至第124册,登载了《大同学》,①暗示消除社会分裂,必须要借助宗教力量。在“今世景象”段落中,《大同学》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其现代通行译文则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
《万国公报》第121册至第124册,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刊载了其他内容,包括光绪政要、华人皈依上帝、经学争论等内容。从其内容可知,当时的《万国公报》对《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只是停留在简单介绍的层面。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作者马克思的国籍,文章前后不一。在“今世景象”段落中,他是“英人马克思也”,在“相争相竞之理”段落中则变为“如德国之马克偲”。即便如此,该报可观的发行量——1897年,月均3200份,1903年,月均4530份——客观上提高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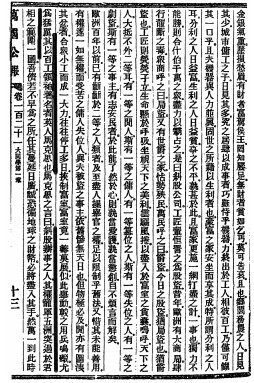
|
1900年12月6日,被冯自由誉为“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的《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月一册洋两角”。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其第2卷11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该文评价“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并强调“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文后列出了26种有关社会主义的参考书,《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这份在日本编辑印刷的华人刊物,异常受欢迎,在一年时间内,派售点即由创刊时的5个,拓展到辐射上海、苏州、杭州、无锡,芜湖、江西、香港、新加坡、东京、大阪、神户和台湾等地的18个。
1903年3月,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该书原为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在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中,该书介绍了马克思(加陆·马陆科斯)和恩格斯(野契陆斯),并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人阶级情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内容。赵必振译文多有不畅,且译名前后不一,大致可反映译者的翻译水平不高或对内容生疏。广智书局在《新民丛报》上所载的广告,则对其称赞有加:“此书关系与中国前途者有二端:一为劳工问题……一为组织党派,……是书析之最详,有志者请急先睹”。③从这则广告上,可管窥彼时的出版界: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不忘做好营销。
同盟会的早期重要成员朱执信,在1905年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对西方思想积极关注,并娴熟地运用现代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派的主张。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县解”在《民报》的第三、第五号,先后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五段话和十条革命措施。朱执信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中,他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害之所由来……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内容所作的较多的介绍”。②毛泽东也评价道: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③同年9月,叶复声在《民报》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④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
1907年12月30日,震述在《天义报》发表《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文章的附录《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同年发表的《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中,震述这样描述共产主义:“我现今有一个好法子,叫你们不要靠人,自然就有饭吃……就是实行共产……”1908年1月3日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序言》,⑤称赞马恩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不易之说”。1908年春季增刊上发表了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为《共产党宣言》作序。文中暗示,作者虽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可通过这本书了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观察以上报刊,会发现:《译书汇编》、《民报》、《天义报》之所以会在日本创刊或印刷,除与当时清政府的言论政策有关外,铅印技术的发达与易得也是一大原因。而广智书局的广告,则反映了彼时的出版市场非常活跃。这一切现象均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媒变革紧密相关。
从传教士报纸《万国公报》到女权报刊《天义报》,从国内出版重镇上海到日本东京,从林乐知到刘师培,均在享受着铅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这些不同背景的报刊媒体与编著者,共同成为了《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者。至此,新式传媒已经深度介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这一现象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又将有新的变化。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整个国家也缓慢地进入了新的轨道。中国传媒行业逐渐成熟,出版印刷行业本身亦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初建的中华民国,虽然暂时结束了改良与革命之争,但是在选择什么样的施政纲领建设国家方面,则暂时未有定论。北洋政府未曾正式提出或采纳过系统的治国理念,这无疑给众多的理论主张提供了更大的争论舞台。在此背景下,各种理论解读和思潮争论,在日渐成熟的传媒领域更加活跃,传媒的政治功用性更强。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更频繁地见诸媒体,报刊对其内容的论述更具有选择性,对其体系解读也更为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各团体组织的理论来源。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报《新世界》第2期登载了《社会主义大家之马儿克之学说》一文。⑥文章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书的纲要,突出了《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十条革命措施。在此之前,该报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为题,翻译连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前三节内容。
1919年3月25日,谭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面面观》发表在《新潮》上。谭平山从政治、经济、精神和社会四个维度,论述了民主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1919年4月,成舍我在《每周评论》名著栏目中,发表了《共产党的宣言》。这篇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10条革命措施,并特别强调“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①
1919年4月1日,《晨报》刊载了渊泉(陈博生)所作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自5月起,《晨报》开始连载渊泉的译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的译文与现在通行的译文已经很接近了。
1919年8月《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刊登了张闻天的《社会问题》一文。张闻天在文章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的10条革命措施。与此前的另一译者叶夏声不同,张闻天已经开始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并解释和宣传共产主义理想。1919年11月,“学生救国会”主办的《国民》第2卷第1号发表了《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一文,并附有译者序。文章内容是对《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翻译。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新青年》杂志在译介《共产党宣言》活动中的表现尤其活跃。在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的《马克思传略》中,刘秉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旨和成书背景,评价它是“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译本”,“书中一语,正如枪弹一射。就其全书言之,几无一语,不经千次之呼吁”。同时期,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八个自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介绍,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解释和演绎,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民国成立后,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报刊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除了当地的读者数量众多之外,现代印刷技术的广泛传播也为这些报刊的出现提供了坚实基础。无论是《新潮》月刊、《每周评论》周刊,还是《晨报》及其副刊,它们的发行量已经很大,出版工作更繁重。没有强大的印刷力量支持,这些工作不可能完成。至于《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和《国民》这些存续时间不长且财力有限的刊物,如果没有已经普及的印刷技术的支持,它们的创办、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印有《共产党宣言》内容的报刊,广为流传,推动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由浅入深地传播。社会进步分子对其内容的认识和积极回应,则更凸显了现代出版技术在传播思想方面的巨大能量。在此情形下,全文传播《共产党宣言》,变得迫切起来。国民党人士和早期共产党人的合作,最终促成了此事。
传媒产业中的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清末民初的印刷技术变迁,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书报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读者群,提高了影响力,也形塑了现代出版产业。彼时的印刷技术经历了从雕版、石印向铅印的转变,新技术的使用影响着出版产业的形态。
坊刻时期,出版活动就已经出现产业雏形。清丰的石印热,催生了点石斋、同文书局、鸿文书局、扫叶山房等大批石印局,产业氛围更加浓厚。铅印技术的完善,为出版机构提供了更成熟的技术保障,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印刷获得更多利润,而利润又为出版行业的技术革新与产业拓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此时的传媒产业版图更为明晰。
民国以后,传媒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壁垒:没有一定的财力做后盾,很难步入出版印刷行业。申报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传媒出版机构,无一不兼具技术与资金优势,其拥有者与决策层均财力雄厚。在这种产业形态中,中小型的传媒出版组织则需高度关注利润,才能与前者并存于市场之中。
利润不止影响传媒机构,也影响相关从业人员。陈望道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①而同时期的郑振铎则抱怨:“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一本书,印书馆就可以赚几十万,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②郑振铎是商务印书馆的正式职工,并且专司“少沾烟火气”的文学刊物。他尚且如此激愤,可见当时出版市场的商业氛围之浓厚。
在当时的上海,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当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者的出版重心集中在教科书上,并且已经基本确立了各自的出版地位和方向。商务此时根深叶茂,需要稳妥的经营方针,不愿做任何有风险的举动,而中华书局此时并没有完全从“民六危机”中走出,经济问题制约着他们的出版选择。出版行业的这种状况,也影响了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传播。
戴季陶、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等人,均热心于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具有日本留学背景,其思想在当时比较活跃、进步,曾接触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对此书极为欣赏,曾考虑将之翻译成中文。1920年,戴季陶主持《星期评论》,编辑部成员邵力子向他推荐了陈望道做译者。陈望道以《共产党宣言》日文本为蓝本③,参考英译本,完成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
按照戴季陶等人的商议,《共产党宣言》译出后将刊登在颇有影响力的《星期评论》上。可惜事与愿违,《星期评论》因宣传进步思想被查封了。商务印书馆此时连新文化运动的节奏都没有跟得上,更不要说印刷这本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译本,竟然“找不到书局印了”。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面临的出版问题,在此时的出版产业背景下,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好在这个经济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建立了又新印刷所,不仅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还出版了其他几种图书④这部深刻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著作,终于在1920年8月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第一版印千把本……” ⑤陈望道译本的初版共56页,为小32开本,采用竖排形式,3号字体印刷,定价大洋一角。初版封面为水红色,再版时改为蓝色。由于排版错误,《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出版时,书名是《共党产宣言》。9月份再版时,改为《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了17版。
彼时的出版行业,为图书做广告已经很常见。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样采用了这种宣传形式。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民国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目,写了一段文字。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 —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整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梁先生校对……
根据“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寥寥数字,大致可以推断出:要么是有购买意向而询问的人确实很多,要么是出版方想营造出询问购买者众多的氛围。无论如何,这则广告目的在于宣传陈译本《共产党宣言》,促进该著作的销售与传播。有意思的是,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在出版中遇到的此类问题,还将继续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其他著作的出版过程中。
《共产党宣言》出版传播中的身份认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出版传播这个论题,已经成为各学科各领域集中发挥作用的“场所”。仔细梳理当时的历史资料,会发现,《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出版、传播和整个社会的进程其实是归化为一体的。现代传媒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化阅读习惯的变化,在推动《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直至成为中国革命指导纲领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传媒在使用者(读者)身份认同构建中的作用入手,进而分析他们对新传媒的运用,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传媒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功用。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时间,中国报刊经历了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不再把传统文化作为主要内容,而是大量刊发社会思想、家庭个人等信息。正如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论述到的一样,新式书报在启迪民智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这不仅在于传递内容,更在于形塑民众接受外界信息时的倾向:更多的人开始对新型报刊持越来越信服和依赖的态度。报刊也逐渐成为了人们了解信息、传达见解,进而施加自己影响的重要工具。包天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饶有趣味地记录了年少时,对每天阅读《申报》的期待和欣喜。①清末著名的四大谴责类小说,正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力量,才能把此前囿于密室、圈子的消息内幕,以书报连载的形式,广为传播。此类记载,在清末民初的各种资料上不胜枚举。
从这些琐碎而细腻的资料和事例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现代出版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范围,同时也初步形成了现代读者的一些身份特征,使他们越来越膺服于现代传媒。越来越多具有相同爱好和兴趣的人士,以现代出版产品为中介,逐渐形成自己的圈子。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传媒主动参与并完成了对现代读者身份认同的构建。而他们也开始在这种共同的身份特征之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回顾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的资料,《共产党宣言》在被国人译介时,虽然不同性质的媒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其中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各种团体刊物。《译书汇编》、《新世界学报》、《天义报》以及后来出现的《新青年》等刊物,均带有较为明显的同人色彩。
《译书汇编》作为留日江苏籍学生的团体刊物,内容以刊登政治学说为主,同时涉及经济、法律、外交和历史等方面。姑且不论其政治主张和观点,仅从内容的定位来看,它对读者就有很强的甄选性。这使得围绕在《译书汇编》周围的学生们,具有相同的志趣。
1902年由赵祖德出资创办,陈黻震、马叙伦、汤尔和等人编辑出版的《新世界学报》,创刊原则是:宗旨不同则敬谢不敏。这一点也证明了,现代传媒在传播思想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对创办者和读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尤其明显。《天义报》是在日留学生中间影响力较大的一份报纸,以无政府主义为其重点宣传内容,在它的旗帜下同样聚集了一批赞同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读者。虽然上述各刊物,关注重心并不完全在马克思主义,但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这些报刊的创办发起者和具体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出版的熟练驾驭者。他们从接受者的角色开始,逐步认识和领悟到现代传媒在传播新知、影响思想方面的巨大能量,转变成了传播者。这些身份转变后的传播者,也开始试图运用现代传媒来影响别人了。这在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尤其明显。
彼时的发起人或者牵头人戴季陶可以说是一名资深媒体人了,在日留学时,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各种文章,先后参与主持过《中外日报》《天铎报》和《民权报》,以“天仇”笔名发表的文章倍受关注,其时正在主编《星期评论》,对报刊的作用恐怕非常清楚。中间推动者邵力子,彼时供职于《觉悟》副刊,熟知报刊对民众的影响。至于翻译者陈望道,《非孝》这篇文章借助现代报纸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想必能使他直接认识到报刊的巨大作用。本来就对《共产党宣言》比较了解的众人,在此情形下,利用现代传媒出版传播《共产党宣言》就是最合适的选择了。
按照传播理论的观点,只有传播者“想象的共同体”一方的努力和行动,并不能够成功地完成一次传播行动。传受两者必须能够对某一话题都产生解码行为,这样一个传播过程才算完整有效。即使受传者本身做出与传者完全相反的解码,也是一种成功,毕竟在受传者那里产生了反应。
处于受传者地位的读者,也是传播成功的决定因素。得益于报刊之前的宣传,《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译本出版之前,民众对其已经有了初步了解。李大钊之所以能够组织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之前的零星式传播。通过梳理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此时,已经出现了一批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读者,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认同又经过报刊的传播得到了确认。
在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许多读者对“青年”、“革命”、“保守”、“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上的新式词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稍后的创造社同样经历了这样一种情况,众多青年读者为了成为所谓“创造”的一分子,也加入到购书的行列,创造了“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四马路泰东图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群的青年所挤满”的盛况。①
受传者和传播者双方共同参与到同一个传播活动中,当然能够确保传播效果,如果再有其他媒介的围观式参与,更能够提高传播效果,至少能够提高影响范围。当其他媒体都在谈论同一话题时,媒介议程设置机制就开始施展自己的功能了。周佛海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谈论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②一时间,“革命”、“青年”等词语成为了一种时髦,谈论此类内容成为了一种“时尚”。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和现代传媒的暗示下,不仅有积极的读者,还有心思活跃的传播者,当然还有其他怕被冷落的传媒,越来越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分子,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建构。
结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至全译本问世,过程可称波折。当时传播者的初衷也许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然而,在他们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下,《共产党宣言》终究走进了中国社会。
晚清以来,新式传媒的出现,不仅促进了西学东渐,传播了大量西方思想,更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形塑了中国社会新形态。其中,传媒、资本、产业和新式社会群体的激烈互动,影响并促成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从只言片语的简介到成章节的解说,再到全书完整出版,现代传媒始终是这一切的平台。
在21世纪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该如何传播?相比清末民初,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而政府也拥有更多的媒体渠道与资源,可以更便捷地从事宣传、引导工作。“如何传播”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已经解决,其实不然。新媒体不断出新,对原有的传媒格局与社会形态同样产生着重大冲击,由此产生的新传媒形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更多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并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更全面更系统地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