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音节性(monosyllabism)常常被视作是汉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赵元任先生说:“如果连同合用而不独立的词都算起来,中国话多数的确是monosyllabic。所以我总说这monosyllabic myth在中国的mythology里是一件最真的myth了。”①当然,有些语料可能违反了“单音节神话”,比如上古汉语大量的重叠词(“窈窕、浮游、蜾蠃、螟蛉”“蜘蛛、踌躇、辗转、契阔”等),或者是双音节的叠音词(如“关关、采采、蛐蛐、肃肃”等)。这些材料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暗示了上古音复声母的存在。上举“窈窕”类重叠词的特征都是后音节均属中古为来母、以母、定母(用字母L统指)且上古读流音的字,这说明它们是PL-、KL-型复声母的一种方块字记录方式。按照近期学界的研究,“蜘蛛”类重叠词实际上则是“基式”(词义重心)在前一音节或在后一音节的假连绵词,实质上它们还是复辅音声母的一种表达方式。
汉语的音节结构类型,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现代,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已有的研究,有些结构性变化值得做些强调。
(一) 从上古到中古从上古到中古,音节内部的声、韵、调三个层面都有的类型变化(音节的结构性变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②:
(1) 复声母的简化:(a)OC.*cC->MC.C-,(b)OC.*Cc->MC.C-。上古音的复辅音声母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前置辅音(c)+基本辅音(C)”型,可出现在此种类型的*c-包括咝擦音s-、喉擦音h-(h-往往是更早s-的弱化式),或鼻辅音m-/n-/ŋ-等,*C-则可以是塞辅音p-/ph-/b-、k-/kh-/g-或鼻辅音m-/n-/ŋ-、流音r-/l-等。第二,“基本辅音(C)+后置辅音(c)”型,可出现的基本辅音的种类与前述*cC-型声母相同,后置辅音主要是流音-r-/-l-(即*PL-、*KL)。第三,“前置辅音(c1)+基本辅音(C)+后置辅音(c2)”型,其中的c1、c2分别是第一类所说的前置辅音和第二类所说的流音类后置辅音,如*skr-、*mpl-等。
(2) Cj-型声母的腭化:OC.*Cj->MC.


(3) [j]介音的出现:OC.-0->MC.-i-。[j]介音是中古三等韵的标志,上古音三等韵与非三等韵字的区别,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设想,不过基本上都同意三等韵的[j]介音是后起的。所以增生[j]介音也是一种结构性变化。
(4) 声调韵尾的消失:(a)

中古音按照实际语音的变化特点,可以分为早期、晚期。早期中古音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中唐,以《切韵》(601)为代表性文献,晚期中古音从中晚唐到南宋,以《韵镜》《四声等子》等韵图为代表性文献。元代《中原音韵》(1324)可作为“古官话”的代表性文献,从元至清代中期可视作近代音阶段,从清代中期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段时间,是现代汉语阶段,跟普通话已无差别。
从中古到现代,北方标准语的音节的结构性变化包括:
(1) 介音变化:-jw->-y-。《切韵》时代的三等介音为[j],合口介音为[w],所以合口三等的介音是[jw]。早期中古音时期四等韵字没有[j]介音,到了晚期中古音,唐宋韵图显示四等韵字已增生[j]介音:-e>-je>-je,三、四等韵合口字趋于合流,所以“冤三渊四”“厥三诀四”两两同音。但[jw]仍为两个音段,直到《中原音韵》的“鱼模”韵还包括了[u](“模”)、[ju](“鱼”)两类韵母,明兰廷秀(1397—1470)《韵略易通》将“呼模”“居鱼”两韵分立,才表明[y]介音的出现。
(2) 韵尾消变:-p/-t-/-k>-0,即中古时期的塞音韵尾[p t k]在北方标准语中逐渐消失。唐宋韵图已可见中古宕江入声字和阴声韵同图的现象,如《切韵指掌图》第十四图有“褒宝报博”“包饱豹剥”。平上去声字韵母相同自不必说,来自入声的“博”“剥”二字是不是也跟其他舒声字同韵,很难说定,但非常相近则是必然。此时“包饱豹剥”的舒、入韵字的韵母,显然不可能是《切韵》前后的[au]—


锐(actue)/钝(grave)和平(plain)/降(flat)两对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是雅柯布森、方特和哈勒在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1951)一书中提出的①。王力先生将这两组特征分别译作“函胡性”“清越性”和“平音性”“降音性”。《初探》指出,声学特征上,钝音是“频谱较低的一边占优势时”的音,锐音是“(频谱)较高的一边占优势时”的音;降音性在声学上则表现为“一组共振峰乃至所有一切共振峰都向下移动”。从音段特征来看,钝音包括后元音、唇辅音、舌根音,锐音包括齿音、舌面音和前元音。平、降特征对立的音,则主要表现为是否唇化(或咽化),比如圆唇辅音是降音性的,腭化辅音是平音性的②。咽化音与唇化音同属降音性音段,“有些民族(如班图人和乌兹别克人)自己的母语中没有咽化音,他们说阿拉伯语词中的咽化辅音时,就发相对应的唇化音来代替,这个事实说明了咽化和圆唇在听觉感受上是类似的”③。OhalaJ.J.(奥哈拉)指出,从调音(articulatory)层面来看,降音性音段包括卷舌音、唇音和软腭音喉音,而且降音性辅音能使后接的元音发生后化、央化或圆唇化④。
下面结合锐钝、平降两组区别特征,着重以若干个案为例⑤,分析汉语音节的结构性变化,从而说明音节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 声母锐钝对韵腹元音的影响(1)中古音阶段真韵、臻韵庄组字的分化⑥
在陆法言《切韵》(601)残卷(如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残卷,编号S2071,学界称之为“切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濂跋本,学界称之为“王三”)、陈彭年等《广韵》(1008)中,真韵和臻韵是两个不同的韵,即主元音不同、韵尾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臻韵字非常少,不但只有平、入两种声调的字,而且只有庄组字。以《王三》为例,平声第十八臻韵共有“蓁搸溱?莘


真韵庄组:*-in(真韵)>*
真韵非庄组:*-in(真韵)>*-in/其他__(MC.真韵)
之所以提出上述假设,原因在于:(a)上述真、臻二韵的庄组字在音节结构层面处于严格的互补分布,而且声韵组合条件明确。(b)现代方言等现实语料也表明,真、臻二韵字的韵母表现是非常接近甚至是相同的。简而言之,我们是用“空格”(slot)组合的方式、“内部拟测”(internal reconstruction)的结构分析方法。
翘舌音是舌尖后音,从区别性特征来看,属于钝音,所以影响到了韵母主元音,使其由锐音性的前元音央化为钝音性的央元音。《切韵》时代臻韵的三等韵庄组字,到了韵图时代,随着庄组三等韵字[j]的失落,被置于二等,亦即“庄三化二”;如果着眼于臻韵字只有庄组字,这一变化也可以称作“臻三化二”。
当然,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何去声的庄组字仍留在真韵,而没有跟平、入声庄组字一样成为臻韵?是调类在起作用,还是词汇条件在起作用呢?如果是调类的不同作用,那么其原因仍待解释。如果是以词汇为条件,那么就是扩散式音变,但正如上述,调类作用(平入与上去之分)很明显,这又不符合词汇扩散的基本条件。
(2)现代吴语蟹、止开三的知系字读圆唇主元音的声母因素
北方标准语中的几类知庄章组字,“滞澄制章世书”(蟹开三祭)、“知知池澄纸章”(止开三支)、“迟澄师生脂章”(止开三脂)、“痴彻芝章”(止开三之),声母都读作翘舌音[tȿ]组,韵母都读作相应的不圆唇的舌尖后元音


现代吴语中,知庄章组字的读音,从音值上看,分作两派,绝大多数吴语与精组字合流,都读作不翘舌的[ts]组,少部分吴语则有的知系字(主要是知二、庄组字)读作不翘舌的组,有的知系字(主要是知三、章组字)读作翘舌的[tȿ]组或舌叶音[tʃ]组。苏南的几个吴语,无锡老派、常熟方言中知系字读翘舌音,其他则都是平、翘舌不分且读[ts]组。尤其特别的是,这些方言的止、蟹开三韵的知系字读作圆唇的舌尖元音。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字的常州老派音是




| EMC | LMC | OM | ||
| 庄 *tȿ- | 照二 tȿ- | 庄章合并 | 照 tȿ- | |
章 * |
照三 tȿ- | 庄章合并 | 照 tȿ- | |
知  |
知  |
知 tȿ- | 知照合并 |
可见,北方官话标准音至晚到元代,知庄章三组声母已合并为翘舌音声母,早期吴语里知三章与知二庄肯定曾有过分立的阶段,这从现代部分吴语(如无锡型)能够得到印证。但是,分立的格局是以什么样的音段区别来体现呢?可以是声母对立,也可以是介音的对立。二、三等韵字的区别在于是否带[j]介音,吴语中蟹止摄开口字读圆唇元音的知系字,只有三等韵字,也就是说只有知三、章组字,而没有知二、庄组字。那些知三章、知二章不分且蟹止开三读圆唇元音的吴语(如常州型),也不牵涉二等韵字。这说明,知三章、知二庄曾经都读翘舌,但由于介音条件不同,导致后来声母演变的结果有别。之所以假设知三章、知二庄两者声母相同而介音不同(而不是反过来声母不同、介音相同),因为这样符合汉语音韵史的发展脉络,中古晚期庄、章合并且介音有别,到了元代以后,知庄章三者合流,读翘舌或舌叶。
之所以出现开口字读圆唇主元音,想必应与声母的翘舌性质密切相关。正如上述《切韵》时代读翘舌音的庄组会使后面的元音[i]央化一样,吴语的知三章组声母的翘舌性质也使得后面的[i]变成了圆唇元音[y]。大部分吴语“平翘不分”,声母从[tȿ]或[tʃ]组变成了[ts]组,但这类字仍然读圆唇主元音。可见,[i]变圆唇的[y]在先,[tȿ]/[tʃ]变[ts]在后。主元音舌尖化则是在[t ȿy]/[tʃy]、[tsy]的音节中发生的,即:
无锡型: [tȿi]/[tʃi]>[tȿy]/[tʃy]>
常州型:[tȿi]/[tʃi]>[tȿy]/[tʃy]>[tsy]>
(1)壮语方言汉借词所见重纽韵主元音变化的介音因素①
重纽韵指的是《切韵》系韵书某个韵中,声母相同、且反切下字不同的两类唇牙喉音字。包括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韵②。在这些韵里出现重纽对立的声母包括帮、滂、並、明、见、溪、群、疑、影、晓母字。按照中古韵书“韵相同,则主元音和韵尾相同”的分韵原则,重纽两类(重纽三等/重纽B类、重纽四等/重纽A类)的语音分别在于介音,重纽三等的介音是钝音性的[ɪ](或作
从中古域外汉字音(如日译汉音、朝鲜译音、汉越音)等材料来看,重纽三、四等区别在中古音晚期仍然很明显。比如重纽四等(包括少量的纯四等韵)的唇音字在汉越音中发生声母齿龈化读[t th z],而重纽三等及纯三等韵字则绝无此现象。朝鲜译音的重纽三等字可见


包括壮语在内的侗台语很早就受到汉语标准语的影响,语言接触导致侗台语各次方言中有不同历史层次的汉语借词,通过观察这些借词的音节结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反观汉语音韵史的早期面貌,重纽三四等字的读音就是很好的一例。下表所举为壮语各方言中止开三见组重纽三等与普通三等韵例字的读音③:(声调省略)
| 骑 | 鳍 | 旗 | |
| 见开三支B | 见开三脂 | 见开三之 | |
| 柳江 | kəəi | ki | ki |
| 宜州 |  |
ki | ki |
| 河池 |  |
ki | ki |
| 上林 | kuui | kei | kei |
| 来南 |  |
kei | kei |
| 贵港 |  |
kei | kei |
| 宾阳 | kuui | kei | kei |
| 武鸣 |  |
kai | kai |
| 凤山 |  |
 |
 |
| 钦州 | khui | khi | khi |
| 隆安 | kooi |  |
 |
| 崇左 | kuui | — | khəi |
| 扶中 | kuui | — | khəi |
| 龙州 | khvi | — | ki |
| 德保 | khvei | — | kei |
| 那坡 | khvi | ki | ki |
中古止开三之韵没有重纽分别,“旗”字在韵图里的位置相当于重纽三等,脂韵“鳍”字、支韵“骑”字所在的韵有重纽之别,所以在韵图里也以重纽三等的面貌出现。中古的普通三等韵虽然没有重纽对立,但其[j]介音在钝音类的唇牙喉音声母的影响下,发音部位也跟着往后移动,变成钝音性的央元音


“骑”字在壮语各方言的读音跟上述朝鲜译音中重纽三等字的介音或韵腹元音的表现如出一辙,即要么是带合口介音,要么主元音是
LMC.* >kəi(柳江) >
>kəi(柳江) > (河池)>
(河池)> (凤山)>kuui(崇左)
(凤山)>kuui(崇左)
>kooi(隆安)
(2)元代八思巴字所见重纽唇音三、四等字的不同表现①
上面的例子主要证明重纽三、四等的不同介音会促使其邻近韵腹元音发生不同的语音变化,所用的语料是壮语方言中的汉借词。下面的例子所用的语料来自元代韵书《蒙古字韵》,该书是用八思巴字(仿照藏文创制的表音性的蒙古字)按照中古以来韵书以韵统字的方式编成的。该书所反映的语音基础大概是元代的北方标准音,比同时代的《中原音韵》显得保守,所以学界认为它是当时读书音的标准音。
《蒙古》虽然不像南宋《切韵指掌图》那样能系统地反映重纽三、四等之分,但唇音字的重纽对立可以从部分韵类里体现出来。总的来说,除没有唇音字的侵、盐韵之外,支、脂、真(入声)三韵的唇音字在《蒙古》中均能表现出重三、重四的不同。以支韵字为例:
碑(支韵帮母平声重三)bue≠卑(支韵帮母平声重四)bi
彼(支韵帮母上声重三)bue≠俾(支韵帮母上声重四)bi
贲(支韵帮母去声重三)bue≠臂(支韵帮母去声重四)bi
帔(支韵滂母去声重三)phue≠譬(支韵滂母去声重四)phi
皮(支韵并母平声重三)pue≠脾(支韵并母平声重四)pi
被(支韵并母上声重三)pue≠婢(支韵并母上声重四)pi
髲(支韵并母去声重三)pue≠避(支韵并母上声重四)pi
糜(支韵明母平声重三)mue≠弥(支韵明母平声重四)mi
靡(支韵明母上声重三)mue≠弭(支韵明母上声重四)mi
支韵重纽三等字标作钝音性的[ue],重纽四等字标作锐音性的[i]。这种分别的格局,与朝鲜译音、汉越音、壮语汉借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其韵腹元音之分的形成原因,就在于介音成分在锐钝不同性质的基础上的后续演变。
三 平降特征与汉语的音系演变锐钝和平降是可以相互交叉的两对特征,比如




下面将分别论述汉语音系中,韵腹元音层面的咽化特征和声母辅音层面的唇化特征对音节内邻近音段的影响。
(一) 降音性与韵腹元音的咽化特征(1)上古三等与非三等韵的元音性质①
关于中古三等韵与非三等韵的来源,国内外音韵学界有着不同意见,包括:有无[j]介音(三等韵带[j],非三等韵不带[j],如李方桂②)、元音长短(三等韵带短元音,非三等韵带长元音,如郑张尚芳③)、声母辅音有否咽化特征(三等韵的声母不带咽化,非三等韵的声母带咽化,如Jerry Norman④)、韵母元音有否咽化特征(三等韵的元音不带咽化,非三等韵的元音带咽化,如潘悟云⑤)。其中Norman用声母辅音的咽化特征来解释一四等韵字,声母在上古带有咽化特征,咽化导致辅音声母发音时舌根后缩至喉壁,从而阻止了可能发生的腭化现象。也就是说,非咽化的辅音声母出现在三等韵中,于是三等韵发生了腭化,即产生了[j]介音;咽化特征作为降音性特征,腭化特征作为平音性特征,两者有截然的对立。
总的来说,归结到标记理论,其实质是一样的。三等韵公认是无标记的(unmarked),一二四等韵则是有标记的(marked)。有标记成分在后来的语言演变过程中往往会向无标记成分靠拢甚至趋同,而不是相反。联系区别性特征来看,比如长元音为有标记特征,短元音为无标记特征⑥。清辅音与浊辅音相比,浊辅音就是有标记的类。同样地,咽化元音与常态元音相比,前者为有标记类。
我们也可以用咽化特征来观察上古汉语的韵母元音,即假设三等韵的韵腹元音为常态元音,非三等韵的韵腹元音为咽化元音。两者在后续演变上不同⑦:
1.上古一二四等字的咽化元音作为有标元音,发音时其舌位要比常态元音偏低偏后。这是发音时舌根后缩的效果所致。
2.以[a]为例,当一二四等字的咽化元音

咽部收缩可以产生降音性效果,对于咽化辅音来说,它可以削弱锐音性后接元音的锐音性;咽化音在听感上和唇化音类似。另外,齿音是锐音性的,而卷舌辅音是降音性同时也是钝音性的。比如在“印度各种语言里,……发卷舌音时,咽部都要收缩,共振腔都要伸长”⑧。
(1)中古音麻佳同韵的声母因素⑨
观察麻二、佳两韵开口字的声韵组合,可以发现二者的特征异同:1.都有唇(帮组)、牙(见组)、喉(晓影组)音字;2.都有庄组*tȿ-字;3.都有知组字,其中麻韵有知组

从声母辅音后接的介音来看,中古音阶段的二等介音可能是由上古[*r]变来的后元音
以泽存堂本《宋本广韵》为例,可知中古音既有麻韵一读、又有佳韵一读的字至少包括:杷(帮组)、




学界一般对中古音韵母的构拟,麻韵读*-a、佳韵读*-æi(二等介音均略去)。两韵的主元音比较相近,但在北方标准语里二者并没有混同的痕迹,只有在中古南方口语才出现麻、佳同韵。要解释两者合并的元音,需要从音节结构内各成分间的影响着手,辅音声母和介音都是降音性的,它们势必会影响后面的韵腹元音。元音[a]和稍高的[æ]都属于平音性元音,但从锐钝特征来看,发音特征属周边性的[a]为钝音,非周边性的[æ]则为锐音。中古麻韵的*-a受到声母及介音(最直接的当然是与之邻近的介音)的影响,周边性特征发生变化,元音舌位抬升变[æ];佳韵的韵母是*-æi,韵腹元音和韵尾都是锐音性,在声母及介音的影响下,高元音韵尾[i]舌位下降,发生*-æi>-æe>-æ音变。从古汉越语和闽语来看,麻佳同韵以后读作锐音性的[e]或者[ε],可见假设麻、佳二韵在中古南方合流为[æ]是可能的。演变的主导因素应是“声介”合母的降音性。
(2)近代以后江韵字合口化的声母因素
《切韵》时代江韵读
在现代北京话中,江韵入声字不论声母条件,都读作圆唇韵腹元音或者带圆唇韵尾,如:剥po1、桌tȿuo1、捉tȿuo1、觉



学界一般认为,唇音字在汉语史上不分开合,尽管像闽语这样较为保守的南方方言,其实可以有唇音字的开合对立,比如泉州方言“霸”pa5、“簸”pua5,但毕竟只占极少部分,而且很可能只是南方方言的特点,未必能够追溯至中古的北方标准语。只有见系字,很明显有另外一条著名的腭化规律(the law of palatalization)在发生作用,即中古音的二等介音



江韵字在北方标准音中之所发生主元音圆唇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可能是中古二等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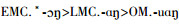


锐钝、平降两组区别特征,在语音学的声学/感知层面的描述有交叉之处,在音系行为上也有趋同的可能。正如雅科布森等所说:“如果一种语言,例如像土耳其语,具有函胡(引者按:即钝音)降音的/u/,函胡平音的/
上文将这两组特征作为观察古今汉语音系变化的着眼点,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钝音性、降音性音段对其邻近音段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探讨汉语音节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是很有必要的。最后列出几点结论,作为结束:
1.早期中古音的臻韵从真韵分化而来,原因在于庄组属钝音的翘舌声母促使韵腹元音发生央化。
2.晚期中古音的止蟹开三的知章组字在部分北部吴语中韵腹元音由不圆唇变圆唇,原因在于知三章组属钝音的翘舌声母促使韵腹元音圆唇化。
3.重纽三等开口字壮语方言的汉借词中韵腹元音变成央、后乃至圆唇的

4.重纽三等唇音字在元代八思巴字材料中转写为合口韵母,原因与壮语方言中来自重纽三等的汉借词的韵母变化相同。
5.上古音阶段的三等韵受到具有咽化元音的一二四等韵的推链影响而增生腭介音。
6.中古南方音中的麻佳同韵,是此二类韵的主元音在具有降音性特征的声母的影响下趋同的结果。
7.中古晚期以后江摄字的韵母由开变合,是其韵腹元音受降音性的声母的影响下增生合口介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