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西方权利概念输入中国以来,国人对权利思想就争论不断,这一争论尤其聚焦于儒学或儒家社会与权利是否相容上。从维新派的热情呼吁到港台新儒家的积极接纳,从保守派的抵御担忧到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汉学家对权利社会的批评与贬斥,从五四激进派的倒孔运动到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敌视,相容论与不相容论都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聚讼纷纭。纵观这些论争会发现,儒学与权利(或儒家社会与权利)及其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澄清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首先概述和简评百年来儒学与权利之关系的几种认知,尤其是不相容论的两种对立形态;接着考察“权利”概念之起源的两种观点,并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的要义与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儒学中的权利思想,或者说用权利话语重构儒家相关思想;最后回应对以权利话语重构儒家思想的异议,并说明此种重构或阐释的意义。
一 儒学与权利之不相容论的两种形态“权利”一词,先秦典籍早已有之,作为名词,其基本含义是权势或权力与利益;作为动宾结构,则意谓权衡利之轻重大小。中国古籍中的“权利”一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源自西方的“权利”概念。首次用“权”或“权利”对译英文“rights”,出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1864年翻译美国人惠顿(Wheaton, Henry)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国际法由清朝总理衙门颁布。该译法虽有争议,如严复便目为“以霸译王”,但它仍然在晚清、民国盛行开来,至今为定译。翻译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笔者遵循一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译法和用法。
自晚清西方权利思想传入吾国,国人对它的认知甫一开始便有了分歧。在戊戌变法前后,国人对是否该引入西方权利思想展开辩论,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热情呼吁权利思想,并试图运用传统思想资源给予论证,“他们都要再三表明自己也是维护儒家伦理的,并力图证明个人权利与儒家伦理不矛盾”。①与此相对,以“中体西用”名世的守旧派张之洞则认为权利思想与中国三纲五常不相容,他说:“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与张之洞同持儒学与权利不相容论,但立意却完全相反的是后来的五四激进派,其典型代表莫如陈独秀。陈氏明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③孔教与权利如何不相容,陈氏说:“(西洋)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故“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④可见,自晚清至五四,关于儒学与权利已经分化为三种立场:(1)维新派的相容论与调和论,当代新儒家基本上继承了此论;(2)守旧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权利论,这一种观点在后五四时代和之者鲜,但在当代却意外地得到了海内外的和声;(3)激进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儒家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派大体上继承了此种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其先驱胡适(见后)。可喜的是,晚近一二十年来,不少中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不再像老一代那么敌视儒家,对于儒学中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发掘,他们乐观其成。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儒家配不上权利论”的声音愈来愈弱的同时,另外一种声音即“权利配不上儒家论”似乎愈来愈得势。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海外持此论的学者多出于对启蒙运动和权利社会的反思,颇有影响的是三位当代美国汉学家,即,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罗思文(Henry Rosement)和安乐哲(Roger Ames)。此三位美国汉学家深受社群主义的影响,他们对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权利个体以及好讼的法律社会多有批评,颇为欣赏儒家的礼仪社群。与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和“权利个体”(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针锋相对,罗思文提出所谓的“角色人”(Role-Bearing Persons)的概念来解释儒家关于“人”的观念,安乐哲则发展出一套所谓的“角色伦理”(Role-Ethics)来诠释儒家伦理。括而言之,这三位美国汉学家关于儒学与权利之关系主要有两个论点:其一,重视礼仪建构的儒家社群中没有孤立的自我,“我就是我的诸角色”,“现代‘权利’概念在古典中国思想中也是完全缺失的”;⑤其二,权利社会问题颇多,借镜儒学可以转换他们的视角。⑥笔者以为,三位社群主义汉学家对儒家所谓礼仪社群的描绘过于理想化,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礼教的批评诚然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无的放矢。他们说儒家没有抽象的自我或自主的自我,不重视普遍原则或普遍性,因而不可能有“权利”概念,虽然多有国人拾此牙慧,人云亦云,但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至于他们对美国权利社会之弊端的批评,诚有矫枉过正的意思,但却并不适用于权利观念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更有影响。
其实,就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而言,在当今中外学术界,不相容论者远不及相容论者主流。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大部分相容论者聚焦于讨论“儒学与人权”。⑦笔者以为,讨论儒学与人权的关系相对容易,因为,其一,从外延上看,人权的范围小于权利;其二,战后人权运动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资源的共同努力,其中自然有儒家的贡献。①从“反向格义”的角度来说,讨论儒学与权利的关系,这要求我们首先厘清“权利”概念的起源与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像不相容论者所理解的那般简单。
二 西方“权利”概念:起源、要义与分类理查德·德雷格(Richard Dragger)在为“语境中的观念”丛书系列之一的《政治发明与概念嬗变》所撰写的《权利》一文中,概述了西方学界关于“权利”概念起源的两种观点。据德雷格,在词源学上,英文中的right及其对应的德语recht和法语droit,都有共同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起源,其早期含义表示做某事符合正确的规范,是正确、对的,这是“right”的客观意义(objective sense)。学者认为,只有right的主观意义(subjective sense)亦即right作为property可以为某人所拥有(have)的用法产生时,才标志着“权利”概念的产生。但是,到底何时出现了right的主观意义?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与它在古典时代的先行词ius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水岭,至于这一分水岭在哪个时间点,则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不可能在中世纪之前发现权利概念。第二种观点以格沃思(Alan Gewirth)为代表,他承认在前现代社会没有办法发现现代权利概念,但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可能有或使用一个概念但却没有一个明白的单词来代表它。”在此看法下,格沃思相继在西欧封建思想、罗马法、希腊哲学、旧约乃至原始社会中发现了权利的概念。在格沃思看来,“权利”这个单词(Word)可能没有出现过,但权利的概念(concept)确实存在。正如德雷格对第二种观点所分析的那样,只要有承认和管理私人财产的规则(如古老的《汉莫拉比法典》),就一定有权利概念,“讨论‘我的’‘你的’就是讨论权利”,希腊人和罗马人肯定没有代表“权利”的单词,但他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谈论权利。关于权利概念的起源问题,到底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诚如德雷格所言,我怀疑词源学的考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有’一个特殊概念”:(1)如果一个人愿意寻找观念(idea或notion)而不管它如何表达,他一定会确信权利概念(concept of rights)与文明社会一样古老,权利概念可能嵌入或分散在古人的许多词汇中;(2)如果一个人坚持表达形式至关重要,那么,权利概念不可能存在,除非有一个单词或短语把它与其他概念区分开来,如此,权利概念最早只能起源于中世纪。②
列夫·温纳(Leif Wenar)在给斯坦福哲学百科撰写的《权利》一文中同样谈到了“权利”概念之起源的两种理解:“迄今为止,权利‘概念’的真正出现仍在争议中,答案在观念史家的能力之外,而在人类学家的领域之内。即便最原始的社会秩序也一定包含一些规则,用以规定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拥有特殊权限履行某种行动。进而,即便是原初的人类社会也一定拥有一些规则,用以说明某些人有资格告诉他人他们必须做什么。这些规则归因于权利(rights)。权利概念是伴随着对这些社会规范的反思意识而自发产生的。……而且,学术争论有时过于乐观地假定概念边界存在明显断裂。”至于“权利”的前现代的“客观”意义何时同时也赋有了我们现代的“一项权利”的“主观”意义,温纳说,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往回追溯:从十七世纪的洛克到霍布斯到格劳秀斯,然后到十五世纪的吉尔松(Gerson),十四世纪的奥卡姆,也许甚至可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格兰西(Gratian)。但他又提及多诺霍(Donohue)现在又证明,权利(ius)的主观意义用法贯穿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后三世纪的古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③
笔者赞同德雷格提到的第二种观点,亦即温纳所谓的人类学观点,其中一个理由固然是此种理解很方便我们讨论儒家的权利观念,但更为根本的理由是,被观念史家所认为现代权利概念起源于那些权利经典文本的近代作者,他们都是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权利概念。我们只要看一看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洛克的《政府论》便不难知晓。霍布斯和洛克都曾说过,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对每一样物都拥有权利。而且,当洛克在《政府论》下篇多次用权利话语解释《圣经》文字时,《圣经》中又何曾有过可以翻译成“权利”的字眼?①
讨论儒学与权利的关系,不仅要了解权利概念的起源,还要理解权利概念要旨及其分类,以便说明儒学中的某某思想对应的是某某类型的权利。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Wesley Hohfeld)对“权利”的概念分析被广泛接纳,据霍氏,“权利”(rights)概念具有四项基本要素(elements),分别为:特权或自主权(the privilege)、请求(the claim,笔者倾向于译为“主张”)、权力(the power)、豁免(the immunity),每一项都可单独构成一项权利。霍氏又考察了与权利概念四要素相对(opposites)或相关(correlatives)的概念,图示如下②:
上表中的“权利”也即是前文提到的“主张权”(claim-rights),亦即霍氏视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权利”。霍氏在一段带有总结性的文字中说:“前作业已充分证明,‘权利’一词常被不加区别地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表达请求权、特权、权力和豁免在内的任何法律利益。然而,狭义的权利却仅与义务相关,也许其同义词‘请求权’更能达义。”③由此可知,霍氏所理解的“最严格意义上的权利”是跟“义务”具有“相关”关系的“请求权”。此对关系可如此表述:如果甲拥有一项主张权,那么某人乙就有一项义务。这种“权利”也是我们下文讨论儒学中的权利思想时最为看重的一种权利。此外,根据英国人权哲学家米尔恩(A.J.M.Milne)的理解与概括,权利的要义就是“资格”:“霍菲尔德宣称‘权利’一词包含要求、特权或自由、权利以及豁免这四种情形,它们都是法律上的‘优势’。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是资格。”④霍氏对“权利”概念的分析主要指向法律权利。实际上,从权利的渊源来看,或者说什么赋予了权利拥有者以某种“资格”,权利可以区分为道德权利(moral rights)、法律权利(legal rights)和习俗权利(customary rights):道德权利奠基于道德理由,法律权利来源于社会的法律,习俗权利来源于地方性的习俗和惯例(local convention)。⑤
以上是“权利”概念之要旨。另外,学界对“权利”的另外两种分类对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也颇有助益。其一,莱昂斯(Lyons)在1970年提出对后人讨论权利概念颇有影响的一对区分,即关于“积极权利”(active rights)和“消极权利”(passive rights)的区分。霍菲尔德式的特权和权力是积极权利,这些权利关注权利持有者自身的行动;主张和豁免是消极权利,这类权利调节他人的行动。积极权利的形式陈述是“甲有权利做某事”(A has a right to ϕ),消极权利的形式陈述是“甲有权利要求乙做某事”(A has a right that B ϕ)。⑥其二,意志自由论(libertarianism)经常把权利区分为“否定性的权利”(negative rights)与“肯定性的权利”(positive rights)。否定性权利的持有者具有不被干涉的权利,而肯定性权利的持有者具有被提供某些益处或服务的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利是一项经典的否定性权利,而获得福利帮助的权利则是一项典型的肯定性权利。否定性权利和肯定性权利都是莱昂斯所谓的消极权利,换言之,两者都是用以调节他人行动的。⑦值得一提的是,法律权利是权利概念的典范,人们经常讨论的“人权”不是法律权利,而属于道德权利;而大部分人权(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主张权,⑧也就是消极权利,这类权利给对方或义务承担者施加某种义务或责任。
三 语言学方法之谬:米尔恩回应麦金泰尔坚持从语言学厘定“权利”概念的起源,并且否定古代社会具有权利观念与实践,乃至更为一般的非议权利,甚至认为西方近代自然权利或人权也纯属虚构的论调,有一位杰出的代表,此即社群主义者兼美德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麦氏的观点是大多数不相容论之否定权利论的最后理据所在,因此,在我们用权利话语重构儒家思想之前,有必要对此观点给予进一步廓清。
麦氏在《追寻美德》中说:“直至中世纪结束前,任何古代或中世纪的语言里都不曾有过可以准确地译成我们所谓‘权利’的词句。大约在1400年前,这一概念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古典或中古语里缺乏任何表达方法,更不用说在古英语里或至19世纪中叶的日语里了。”根据他所提供的语言学事实,他认为:“存在这种仅凭人的资格就赋予人类的权利,当然有些不可思议。”他甚至断言:“自然权利或人权全属虚构”,“相信它们如同相信女巫和独角兽”。①麦金太尔对权利思想本身的非议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和“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立场与观点,②是大多数儒学与权利不相容论者的最后理据。然而,对于麦氏此种看法,英国权利哲学家米尔恩如此回应:
依麦金太尔之见,在希腊语和其他古代语言里不曾有过我们所谓“权利”一词。可是,在《菲多》(Phaedo)里,苏格拉底的临终嘱托是,“克立同,我欠阿斯克勒庇乌斯一只鸡,你会记得还债吗?”显然,说欠某物,即是说应该给被欠的人以偿还。这与说后者被授予权利是同义的,即某人有权利获得偿还。希腊人没有能从字面上译成我们所谓“权利”的单词,但他们显然有对权利概念的有效理解。事实已表明,希腊语里有可以从字面上译成我们所谓“应得”(is due)的词语。何况,我们的“权利”一词也非单义的。依霍菲尔德之见,权利一词表达四种不同的概念。它们是要求、特权或自由、权力以及豁免。若其中某一概念的持有者应该得到尊重,该概念就表示权利。这由法律、道德和习惯来确认。不过,怎样表示尊重和由谁来表示,则因事而异。不必过分拘泥于这样的事实,即一种语言里的词句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单个的同义词。在后一种语言里,可能有另一些词句,它们的使用表明讲话者对于在前一种语言里由单词表达的概念有相通的理解。麦金太尔作为论据引用的一切社会都不曾发现权利概念的语言学事实,是无关宏旨的。③
米尔恩通过希腊人虽然没有可翻译成“权利”概念的对应词汇,但希腊人却毫无疑问有对权利概念的有效理解与实践这一简单事实,来说明麦金太尔试图通过语言学的考察否定古代社会没有权利观念的论据根本无关宏旨。
诚如米尔恩所言,麦金太尔的论证是错误的,与其考察“权利”概念的语言学事实,不如考察古代社会的财产制度和承诺的做法,他接着说:“财产制度的某种形式为社会生活所必需。没有它,社会成员就无法占有、分配、使用和维护团体和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承诺也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成员就不能签订并执行协议,就不能从事制度化合作,而这种合作正是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这些制度和做法均由规则来构成,规则必然要授予权利,而不论有没有单个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权利。财产规则必定授予人们获取、转让物质资料和劳务的权利。承诺规则必定授予受约人要求守约的权利。”④凡是有财产制度与承诺实践的社会就必定存在权利(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对那些没有受过哲学训练从而也是没有任何哲学立场的贩夫走卒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日用而不知(对权利概念能有效理解与运用,但却不知道“权利”这个词汇)的简单事实。下文就让我们运用权利话语来阐释或重构这些存在于儒家思想与实践中的日用而不知的权利观念,使之显现出来。
四 古典儒学的权利思想重构根据前述有关权利概念之起源的人类学理解以及米尔恩对麦金太尔的回应,任何古代的思想世界与社会实践都必定存在着权利的观念与实践,儒学与儒家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下文主要聚焦于孔、孟、荀的行事与思想来阐述儒家的权利观念,或者说,将使用一套权利及其相关的话语来重构孔、孟、荀的一些相关思想,并尽可能说明他们的思想所对应的是哪种权利。
(一) 孔子:无讼不必否认权利,美德亦未必导向良俗根据人类学的理解,权利现象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以儒家为例,《礼记·礼运》所虚设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可能没有权利观念,然而“货力为己”的小康社会必定是已经有了权利观念的社会。而且,我们必须铭记,孔子所致意的是小康社会,也就是“礼义以为纪”的社会,礼义是古人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基本体系。中国古代被认为缺乏权利意识,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人被认为缺乏契约精神与实践。果真如此吗?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契约实践与相关制度。《周礼·司寇·司约》云:“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①这里记载了“司约”的职务是管理契约券书。这些契约券书有的涉及邦国之间,有的涉及万民。其中“治民之约”“治地之约”“治功之约”等必定涉及今人所谓的权利。若有因权利不明或争权夺利,产生纠纷而诉讼,那么,司约就开府视察契约券书,不守约者处以墨刑。今人一般认为《周礼》为战国时作品,这一记载表明,彼时社会关于民事、土地等契约的实践必然不少,否则不可能专设一官以处理此事。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②契即契约,犹今之所谓合同。“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意思是债主虽执券约而不要求债务人偿还。这当然是反权利的思想。与老子思想不同,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③陈祖为对此评论道:“当我们被他人误解或伤害时,孔子说诉讼公平或正义是适当的。孔子对调停、协调和妥协的偏好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权利,也不意味着当人们受到伤害时他们不应该运用权利来保护自己。”④非议儒家权利论者常以孔子“无讼”之说为据,“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⑤然而,亦如陈祖为在回应儒学与权利不相容论者的理由之一即“儒家社会的非诉讼特征”时对孔子此语评论说:“孔子并没有说诉讼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绝对避免。”⑥实际上,礼乐刑政并用,实儒家治国理政之一贯主张,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⑦岂能以一句“无讼”而全盘否定儒家礼乐刑政并用之法。比较老子与孔子的说法,我们会发现,孔子显然比老子更具权利意识,因为即便是“无讼”,那也要通过调停的方式解决权利冲突,使各得其应得,而不是和稀泥(作为仲裁者)或一味退守辞让(作为权利持有者)。因为重视“以直报怨”的公正意思,所以“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⑧,他也盛赞子路“片言可以折狱”,⑨盖子路心无私欲邪曲且果敢正直,故仅凭两造之只言片语便可公正断案。诚然,《荀子·宥坐》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①但只是表明,孔子认为家庭尤其是父子之间的纷争不应诉诸诉讼和权利的手段来解决。如果父子间的纷争动辄即诉诸权利手段,那确实是权利之滥用。
孔子的权利意识在他评价子贡和子路做好事后的后续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吕氏春秋·察微》篇载: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②
根据鲁国法律,若有人赎出在他国为奴婢的鲁国人,此人便拥有从国库中获得补偿的权利(这当然是一项法律权利)。子贡赎鲁人于诸侯,归来后却不接受政府补偿。子贡放弃其权利的行为无疑展现了他辞让的美德,然而孔子却对他给予责备,因为若此以往,则没有更多人愿意救赎在外为奴的鲁人了。相反,若子贡接受了政府的补偿,那么就会激励更多的鲁人救赎在外为奴的鲁人。与子贡不同的是,子路曾拯救落水者,落水者谢之以牛,子路并不辞让而是心安理得接受(这可以视为一项“习俗权利”)。一般认为,子路的美德可能没有子贡那么高尚,可是,孔子却颇为赞赏子路,因为这将导向人们拯救落水者的良好风尚。这两则故事尤其是孔子的评论表明,孔子并非一味强调礼让的美德,而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权利意识。而且,孔子无疑相信,权利的正确行使有利于形塑良好的社会风气;相反,礼让虽为美德,但若应用不当,反而会挫败社会风气,故《淮南子·齐俗训》总结云:“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③
(二) 孟子:个人权利与百姓福利权的捍卫者在先秦诸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当中,孟子的个人权利意识最为强烈,作为士之自觉的代表,孟子一方面批判彼时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枉尺直寻,行妾妇之道,游说诸侯,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正当利益亦毫不讳言。彭更质疑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④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彭更质疑孟子尸位素餐,无事而食。孟子于是讲了“通功易事”的重要性,并且把自己“为仁义”的职业与梓匠轮舆做了类比,既然梓匠轮舆等手工匠人可以通过劳作以及与他人通功易事而获得报酬,我孟子为仁义反而不如梓匠轮舆吗?孟子之意,正如匠人可与农民和女工通过交易而获取各自的生活所需,为仁义之士也可以从诸侯或跟随者那里获取生活所需。交易当然蕴含了财产权的观念,而且某人通过劳作和交易也就获得了对某物的主张权。
这当然不是孟子为自己利益辩护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毋宁说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如他所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⑤在孟子看来,利益之取与不在于利益之小大多少,而在于它是否符合道义,对于某人来说符合道义的利益便是他的权利。其实,胡适早已注意到孟子此论所蕴含的权利思想,他甚至建议把“right”翻译为“义权”:“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后来才变成法律给予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中国古代思想也未尝没有这种‘义权’的观念。孟子说的最明白:‘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正是‘权利’的意义。‘一介不以与人’是尊重自己所应有;‘一介不以取诸人’是尊重他人所应有。”⑥
如前引米尔恩所言,只要有财产或承诺的制度,相应的规则就必然会授予权利。恰好,孟子对此两个方面都有论述。我们先看孟子对财产制的论述。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因此,他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① “恒产”当然意味着某种财产权,而“经界”则意味着对财产的分配与界限,亦即权利归属的确定。在孟子看来,正“经界”是为了防止暴君污吏对民人财产的侵犯。孟子又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②民有恒产的需求和主张,而君主则有制民恒产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说正经界防止暴君污吏的侵犯对民人来说是一项前文所说的否定性权利(negetive right),那么民人要求君主制民恒产则是一项肯定性权利(positive right)中的福利权,两者都属于消极权利(passive right),因为他们都是用于调节他人(在此即君主或政府)的行为,两者对统治者都施加了某种义务。
我们再来看孟子对承诺的论述。《孟子·公孙丑下》载: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③
韩国学者李承焕在讨论儒家的权利观念时,也曾注意到孟子此论,并用权利与义务(或责任)的术语来阐释此段文字:“这里,许诺人受委托在其朋友外出时照顾其家人,不只是处于给予其施舍的立场,而是处于有责任有义务照顾他们的立场。家人(第三方受益者)有权利得到许诺人的照顾。……家庭成员有权利获得许诺人的照顾,他们可以抱怨并维护他们的权利。……承诺不仅是一种慈善的保证,而且是确保相关的另一方(或者第三方,当第三方受益者被考虑时)能够选择做出选择的努力。”④ 《孟子·公孙丑下》又载: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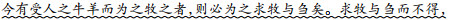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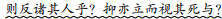
李承焕单独引用了划线部分,并同样用权利与义务的术语转译了一番:“无论其情况是两个朋友之间的承诺还是两个立约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牲畜的所有者有权利使其得到照顾,而且当诺言未被履行时他也有资格要求它们被返还。另一方面,被委托方有义务照料牲畜,并且有责任将它们返还给其主人。换言之,牲畜的所有者即是权利持有者(牲畜则是第三方受益者);而受委托照料牲畜则是义务的承担者。……从这里我们注意到,尽管没有使用‘权利’一词,权利观念明显地包含于《孟子》的语句中。”⑥质言之,承诺的规则授予受委托人某种义务,同时也授予委托人某种权利。笔者进而要指出的是,孟子上述两个承诺的例子,都是想通过此种类比推理来表达统治者与其民人的关系,换用权利与义务的术语便可转译如下:统治者有义务照顾好其民人,而民人亦有权利要求被照顾好——这项权利是前文所说的“肯定性权利”中的福利权,因为它要求统治者给民人提供某些福利;同时它也是一项“消极权利”,因为其规则是用于调节他人(统治者)的行为。孟子进而认为,如果当统治者没有履行其义务照顾好民人,则民人可以置换之乃至革命。正如孟子对“汤放桀,武王伐纣”的理解那样:“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⑦这可以视为孟子捍卫民人反对暴政的权利或者说反抗权。
如所周知,孟子的思想以仁义著称,何谓仁义?孟子有一简单明了的否定式界定:“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①如果说“仁者爱人”或仁要求我们同情处于悲惨境地的他者,这是仁之美德的表达;那么,此所谓“杀一无罪,非仁也”则是一种原则(杀无辜者是不对的)或权利(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的表达。同样,“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也不是义之美德表达,而是一种原则表达(盗窃是不义的,也就是不对的)或权利表达(物主对该物拥有所有权)。亦如李承焕所言:“义与西方的正义与权利概念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简言之,义是所有人类给予或索取、预付或提取的行为标准,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每个人的权利与责任。”②孟子说:“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③穿踰即穿穴踰墙,比喻盗窃行径。盗窃是对他人财物的一种损害。格劳秀斯是西方近代权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在谈及“权利的源泉”时即把“戒绝觊觎他人的财物”包含在内。④孟子又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⑤此一论断表达了罗尔斯《正义论》中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⑥罗尔斯是当代道义论的杰出代表,其《正义论》所要反对的主要对象是长期在英语世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罗尔斯批判功利主义的一大原因在于他认为后者无法有效保障个人权利,而他的这一论断则是对个人权利之至关重要性的申明。
最后,若所周知,“尊严”是现代人权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而孟子的人性论尤其是他所谓的“天爵”“良贵”说蕴含了深厚的内在尊严的观念,这一点早已为不少学者所论证。罗哲海说:“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人权观念提供了直接关联,且是唯一的直接关联。因为依照孟子的观点,通过人的本性,人被赋予了天然的内在的‘尊严’,先于任何可能以后由国家、社会赋予的外在尊严。”⑦关于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联,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引乔尔·弗因堡的话表达得简单明了:“尊重人可能很简单,就是去尊重他的权利,这两者不可分离,而被称为‘人的尊严’的这种东西可能仅仅就是确证这些权利的、可辨认的能力。那么,去尊重一个人,或者说他拥有人的尊严,就仅仅是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要伸张权利的人。”⑧
综上,孟子对财产制度、承诺与市场交易的论述表明,彼时社会必定拥有了今人所谓权利的观念与实践,孟子大概也是第一位明确为自己权利(亦即正当的个人利益)辩护的儒家,同时他也积极关注民人的福利权,这两者都对君主或政府施加了某种义务,而一旦后者没有很好地履行其义务,那么,孟子认为人民也就具有了反抗权。
(三) 制礼义以分之:荀子关于权利的制度化构想如果说孟子系通过个人权利和百姓福利权一方面来反抗暴政,另一方面反对战功功利思潮;那么,荀子则主要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如何安顿社会成员的利益,其思考主要体现在他常说的“制礼义以分之”的社会政治哲学构想中。
《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⑨这是荀子对礼之起源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礼之功能的阐明。荀子认为,在前礼义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欲望,因为彼时还没有度量分界(也即是权利没有归属),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欲求他所欲求的东西。如此,人们之间的欲求必然冲突与纷争,最终结果必然是普遍地陷入乱而穷。为此,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也就是使被欲求之益品通过礼义这一套制度而得到度量分界,从而使权利有所归属,这样就不再有纷争,从而也就不会陷入乱而穷的悲惨境地。这是荀子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荀子一再论之。《荀子·王制》云:“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①荀子在此提到先王之所以制礼义的三个既定前提:一个是“势位齐”,在没有等级的前礼义状态中,每个人大体是平等的(类似霍布斯所谓的“自然平等”);一个是“欲恶同”,每个人的欲求和厌恶的东西大体相同(类似霍布斯的“趋利避害”);一个是“物不澹”(澹通赡),物质条件总体上并不赡足,不能满足每个人的欲求,当然也不是极度的贫乏(类似休谟所谓的“正义的环境”)。在“欲恶同”这一人性事实与“物不赡”这一物质事实都无法改变的条件下,欲达正理平治,只能改变人之“势位齐”,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别上下、贵贱、贫富等,以便使得社会各阶层各职业之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得到确定。荀子举例说:“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②人情好逸恶劳,若权利归属不定,则人们有争功之祸。又说:“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③只要权利明确,得其应得,则受天子之位、禄以天下亦不会自以为多;做一些监门御旅、抱关击柝等卑微的事务以养家糊口,也不会自以为少。
在荀子的论述中,与“礼义”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分义”。“礼义”是从社会制度或社会体系而言,“分义”是从社会成员或主体而言。在此区分中,“礼义”类似于前文所言的“right”的客观意义,表示社会的规范,遵循礼义而行是正确的;“分义”则类似于“right”的主观意义,表示某人的分义,亦即某人之权利与义务。“分义”兼有今人所谓“权利”与“义务”两义。《荀子·君子》篇云:“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④圣王以礼义治国,社会成员皆能明自己之分义,具体言之:士大夫、百吏、官人皆恪守其职,这是言说义务;众庶、百姓皆各守其业,无有奸怪之俗、莫敢盗窃他人财物,这是言说权利。《荀子·大略》亦云:“国法禁拾遗,恶民之串以无分得也。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 ⑤国法禁止社会成员拾取他人遗失的东西,这是防止他们养成不按照等级名分去获取财物的习惯。接着,荀子用一大一小的例子来彰显“分义”的重要性:若有分义,各得其应得,则受天下而治不为贪;若无分义,则即便妻、妾名分亦难定,由之不能齐一家,遑论治国平天下。⑥
荀子的这些诸多说法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前引孟子之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两者都表达了权利及其界限的思想。不同的是,孟子由内在而普遍的心性来确定“道义”的标准,荀子则通过客观化的礼义来确定“分义”的标准。
梁启超与萧公权在论述荀子的政治思想时,早已使用了权利话语来给予阐释和分析。梁启超说:“慎子又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荀子之以分言礼,其立脚点正与此同。质言之,则将权利之争夺变为权利之认定而已。认定权利以立度量分界,洵为法治根本精神。”⑦萧公权说:“盖荀子认定‘人生不能无群’,必合作分工,然后可以图存。然人性既恶,则合群生活之中势必发生二重困难之问题。一曰个人之权利不定则争享受,二曰个人之义务不定则怠工作。解决之道惟在制礼以明分,使权利与义务皆确定而周知。”⑧梁、萧二氏的见解和诠释无疑是十分恰当的,他们都从荀子“分”或“明分”的概念中发现了现代“权利”概念的雏形。
五 对质疑儒家权利思想的回应如前提及,汉学家的“权利配不上儒家论”在现在似乎得到不少国内少壮派儒家或儒家同情者的附和,尽管他们对儒学的认知与三位汉学家不尽相同。他们在思想上多受到黑格尔主义、社群主义、美德伦理学的影响,认为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过于单薄乃至浅薄,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社会并不可取(其实这与是否需要权利是两回事);在方法论上,他们多受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和“不可公度性”或剑桥思想史学派所谓“语境中的观念”以及他们常说的“范畴误植”或“时代错乱”等概念的影响。我在一些同侪的学术会议上经常会感受到此种论调,但就此撰文严肃讨论此问题的,似乎只有友人黎汉基先生对我曾经用权利概念诠释儒家思想提出质疑与批评,他的质疑表达了“权利配不上儒家”论的几条重要论据,值得认真对待和回应。
笔者曾多次零散地使用权利及其相关概念来诠释儒家思想。黎汉基先生在《儒家的权利观念?——疑难与反思》一文中批评鄙说,他的批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一,他说:“在陈先生手中,‘利益’、‘权益’、‘权利’、‘正义’诸词的涵义似乎是互相转换的,但在英语上,interest、entitlement、right、justice等概念肯定不是同一回事。”①我的论述当然不是混淆这些概念,事实是,讨论“权利”概念而离开这些相关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前引米尔恩所言,权利(right)的核心要义即资格,而权利无非就是正当的利益(interest), 德国法学家耶林便说:“据我自己的定义,权利自身不外是一个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②一个人获取其正当利益或保障人们正当利益的制度自然是正义的(justice)。实际上,当我带着这个批评再次阅读权利哲学的本文时,益加发现这些相关概念俯拾即是。
其二,黎先生进而根据笔者前引德雷格的研究,说明“rights”有“主体性构想”(表示正确、对的、公正)与“客体性构想”(表示一项权利)之区分,然后说:“陈先生的例证充其量只能证明儒家在某些情境下不赞成人命遭到危害,滥杀无辜是不对的,或得到某些好处没有问题;孔、孟、荀三人所说的话都是针对他们特殊的情境而发;他们都是表述了‘对’或‘不对’的判断,并非申明人们该拥有的权利。改用英语翻译的话,仅能用it is not right that...来理解像‘杀一不辜’之类的说法,不能预设the people have a right of live。换言之,先秦儒家只有right的‘客体性构想’,而非‘主体性构想’。”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批评很要害。然而,笔者以为,在孟、荀那里,“义”实际上兼有主客两义。“义”可以表示道德上之正确或对的,是为一客观原则。前引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里的“道”“义”侧重客观意义的表达。但是,当孟子明确运用道义的客观义为自己的利益辩护时,它便转变为一种主体性构想。考虑到孟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③以及“天爵”“良贵”之论所表达的人性平等和内在尊严的观念,孟子有此主体性构想一点也不稀奇。再如,在荀子那里,“礼义”多表示客观规范的意义,“分义”则多表示主观的意义。进而,笔者以为,right的主、客观意义并非截然两分,毋宁说是一体两面,只是立论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在西方权利观念史上的某个恰当时刻,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从ius或right的客观意义中转出了其主观意义,如前所言,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水岭,而有的学者则质疑他们过于乐观地假定概念边界存在明显断裂。从人类学的视域看,而不是从语言学的方便法门看,笔者认为后面一种观点也许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而且,断裂论者总能把ius的主观用法由近代不断往前推至中世纪乃至古代的罗马希腊社会,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
其三,黎先生进而又批评说:
陈先生误认儒家存在right的“主体性构想”,其内在逻辑不难理解。他的主要想法,是认为人应得什么,或做什么是对的,必然预设着权利的存在。这里有两点疑问:(1)“应得什么”的“应得”在英语中是deserve,哲学惯用的术语是desert一词。“应得”什么,跟是否具有相关的权利,显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应得什么,跟这是正确的(it is right)或X君具有某种权利(X have a right)并不相同。M小姐虽然丽质天生,其艳无俦,但不等于她应得到世人赞颂的权利。罗尔斯(John Rawls)说:“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所占的优势,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最初有利出发点一样——这看来是我们所考虑的判断中的一个确定之点。认为一个人应得能够使他努力培养他的能力的优越个人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他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环境,而对这些条件他是没有权利的。‘应得’的概念看来不适应于这样情况。”……他(罗尔斯)把“应得”与“权利”予以明确划分,是足够清晰的。
此批评的要点在于质疑“应得”与“权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为笔者把“应得”理解为“权利”。然而,研究权利概念起源的塔克的一段论述,却表达了“应得”与“权利”之间的关联,他说:“他们的权利(ius)就是他们的权利主张[应得(meritum)]。”①再如,前引米尔恩说:“希腊人没有能从字面上译成我们所谓‘权利’的单词,但他们显然有对权利概念的有效理解。事实已表明,希腊语里有可以从字面上译成我们所谓‘应得’(is due)的词语。”又如,首次使用“权利”对译“right”的丁韪良说:“既如一‘权’字,书内部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②可见,丁韪良便是用“理所应得之分”来界说“权利”。前引胡适一段话中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也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应得(胡适名之“应有”)是权利概念的内核。凡此种种论述,莫不是把“应得”与“权利”联系起来,甚至把权利界定或等同于应得。至于黎先生所引罗尔斯反对“应得”的一段著名论述,那只是罗尔斯的一家之言,他的同事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不赞同。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罗尔斯之说,即便如此,我以为罗尔斯对“应得”的反对情形(如自然天赋、最初有利的出发点以及有赖于幸运环境的个性发展等)并不适用于孟子基于人性平等的应得学说,因为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③罗尔斯反对的那些应得情形都属于孟子所说的“求在外在”,基于这些运气或偶然成分的应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但是仁义礼智等德行是“求在我者”,他们并不需要幸运的家庭或环境,基于这些因素(即德行)的应得当然是比较合理的。黎先生所举M小姐天生丽质的例子属于自然天赋,只能说明罗尔斯反“应得”的情形,而不能说明孟子所论的梓匠轮舆以及他为仁义的情形。
其四,黎先生的最后一个批评,由非议用权利来诠释儒学进至非议权利本身的普遍性。黎先生说:“陈先生强调儒家拥护个人权利,立论背后乃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一个共同预设,就是相信凡人皆有权利,不言而喻。这不是陈先生的个人私见,像政治哲学家诺齐克也是这样想法。……然而,权利——‘主体性构想’下的right——并非自古皆然,更非所有地方皆有,而是西欧中世纪晚期的独特发明。……以上结论可以说明,把政治想成一套正当建构的权利,是西欧政治观念独特的历史发展;因此,我们也不必预设儒家也必是这样的思考进路。”如前所言,这是非议儒家权利观念的最为常见的一个论据,即质疑权利的普遍性,强调权利是西欧中世纪或近代的独特发明,不能离开语境而使其普遍化。这个批评与前引麦金太尔的非议如出一辙。然而如前所引,米尔恩对麦金太尔的回应指出此种论据根本无关宏旨。黎先生又引用港台新儒家李明辉先生的说法:“‘人权’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都付诸阙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后说我把权利概念投射到儒家经典之上,“显然呈现了某种形式的时代错乱的问题”。但是,诚如前引德雷格所言,对于一种学说或社会是否“有”权利概念之“有”,本身即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强调表达权利概念之关键术语的重要性,认为权利概念的起源不会早于中世纪;一种则认为术语表达无关紧要,权利概念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坦率地讲,我对德雷格此文的注意,得益于黎先生的批评,但黎先生只引用了他认为有益于其观点的论据,却不曾引用德雷格此说(实际上德雷格只是概述西方学界的不同观点),难免有失公允。实际上,李明辉此文正是就儒学与权利做一种“重建的调适诠释学”,以说明儒家完全可以接纳权利,至于他说儒家连权利概念也付诸阙如,只能表明他对有无某一概念之“有”的理解是上述第一种理解,而在我看来,他的实质工作却完全表达了第二种理解。总之,关于古代社会或儒家思想中是否具有权利观念,与其说是有无的问题,不如说是多少的程度问题。笔者当然不会否认,近代西方是权利理论的高峰期,现代西方是高度发达的权利社会。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和儒家思想中的权利思想相对薄弱,这也正是笔者要挑出儒家思想中这些可贵的星星之火,特别给予阐发的缘由所在。
最后,有必要挑明的是,笔者的基本看法当然是,权利社会有其高度的合理性和可欲性,它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坏处。更一般地看,很多非议权利的人士都把权利个体与社群理想对立起来。在笔者看来,实乃皮相之见。实则所有基于原子个人的契约论者,从霍布斯到罗尔斯,他们的目标指向的都是如何使社会成员更好地合作。如果我们只留意他们的方法论前提或预设即原子个人,而忽视他们的理论目标即社会合作,然后断言权利个体必然反社会,岂非自欺欺人。至于有的人士一听到“权利”二字就联想到自私自利和争权夺利,那更是不着边际;因为权利固然是一种要求或主张(如霍菲尔德所言,在其最严格和狭义的意义上而言),但必须是正当性的要求或主张才是权利,而且人我群己之间的权利(孟子所谓“正经界”和荀子所谓“度量分界”)恰好构成了对某一主体权利的限制。在笔者看来,很多国人非议或担忧权利,多半出于对权利的不理解。有的人士非议权利是因为权利话语的泛滥,但笔者以为,问题不在于权利话语的泛滥,而在于从每个人所声称的权利中辨别出何谓真正的权利,这愈发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权利而不是放弃权利。
还有一些人士充分肯定权利思想与权利社会的可欲性,他们不非议权利,但非议儒家权利。在他们看来,既然权利是个好东西,而西方的权利理论又发展得很充分,我们直接引进就行,何必如此曲折地探讨儒家权利或试图从儒学论证权利。果能如此,本人乐观其成。然而,首先,笔者对此颇表怀疑。诚如美国学者萨姆纳·突维斯(Sumner B.Twiss)所言:“即便人权的正当性可以通过道德传统的道德洞见与责任承诺的重叠共识来证明,考虑到文化多样性,它们也必须用适合其自身的道德术语来论证甚至阐明。”①突维斯此论乃就儒学与人权而言,我想儒学与权利之关系亦是如此。换言之,我们很有必要从儒家的思想文化与道德术语来论证和阐释权利,权利思想才能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落地、开花和结果。其次,权利理论发展至今,大多数肯定权利的西方学者,都不承认之前权利哲学的种种根据是绝对牢靠的。在此方面,艾伦·德肖维茨(Dershowitz,A.M.)对西方传统的“自然权利”或“上帝赋权”等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因为在他看来,不同的立场都可以诉诸“自然”和“上帝”,他认为权利源自不义的经验。针对西方传统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他提出所谓的“培养权利”(nurtural rights)②。这倒与更少形而上学预设的古典儒家尤其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而且,如前所述,孟、荀中的权利思想主要与他们对义与不义的理解相关。“培养权利”的概念也启示我们,很有必要从自身的文化与经验中培养权利。


